发表于《西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精读收藏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导出/参考文献 分享 打印 摘 要: 近代以前,荷马研究是在语文学视角下进行的,语文学考证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无法超越文本本身,只能通过作品保留的信息来还原创作的过程。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口头传统”理论弥补了荷马研究中单一的语文学考证的不足,将史诗创作放置于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背景下,还原了史诗的表演现场,为寻找“真实的荷马”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口头传统”作为一种创作的形式所反映的是希腊社会早期的历史和文化。 关键词:荷马问题;语言学;口头传统;古典学;希罗多德;特洛伊战争; 作者简介:张绪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20-09-10 基金: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林志纯先生与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2018BS16),项目负责人:张绪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林志纯先生与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SWU1809696),项目负责人:张绪强; Oral Tradition Theory and Homer StudiesZHANG XuqiangAbstract: From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onwards,scholars tend to interpret the so-called “Homeric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with a focus on the written texts of the epics.The oral tradition theory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Homer in the context of oral composition.It places the epic creation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text,restores the epic performance scene,and finds a new approach to “real Homer” .The oral tradition theory sheds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early Greece and also shows a promising future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trend in current historical studies.
Received: 2020-09-10
荷马史诗的研究大约开始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100年左右,亚历山大里亚一派渐趋成熟,这一时期的荷马研究为后世的学术讨论树立了典范,成为西方学术的源头[1]。荷马史诗的创编方式、史诗作者以及成书年代等是学界讨论的重点问题,因为长期没有确切答案,话题常谈常新,所以学界把此类问题称为“荷马问题”。有关“荷马问题”的讨论已历数个世纪,学术界在开展专题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学术史的梳理。韦斯与斯特宾格于1962年合编的《荷马研究手册》收集了多位学者的综述文章,成为近几十年来开展相关荷马研究的起点 [2]1。该手册高度关注了兴起于美国学界的“口头传统”理论在解决“荷马问题”中的里程碑意义及其对荷马研究的启发作用。我国学界也逐渐关注到这一研究动向,老一辈学者左景权和罗念生较早认识到荷马史诗的口头特征。近年来,随着古典学术的推进,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与“口头传统”理论密切相关的“口头程式”理论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3]72。在介绍相关理论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这一理论解决荷马研究中的问题。晏绍祥在考察荷马社会的“城邦萌芽”时曾开辟专门章节讨论荷马社会的口头传统[4]。张巍长期关注古风希腊诗教传统,其研究理论即来自美国学界对希腊社会“口头传统”的研究,曾撰文讨论尼采对“荷马问题”的贡献[5]32。当然,“口头传统”理论也受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挑战,[6]19史湘洁等认为荷马真有其人,并曾游历到过埃及[7]198。将“口头传统”理论放在荷马研究的整个学术史中来考查,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理论对荷马研究的意义。 一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斯(Peisistratos)之前,人们对荷马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有限的记载集中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典著作中。戏剧家克塞诺芬尼斯(Xenophanes)和诗人西蒙尼戴斯(Simonides)较早地提到了荷马这个名字;希罗多德最早提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个名词。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促使人们更多关注到荷马史诗所记载的更为久远的那次希腊世界与东地中海城邦之间的战争,希波战争被史家们有意识地与特洛伊战争作为比较看待的两个对象。所以,此后记载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也开始受到古典作家们的关注。从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古典作家对荷马史诗的一些认识,他们大都把荷马看作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这位伟大诗人及其两部史诗都推崇备至[8]。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开始较为频繁地提到“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三个名词。同时,寄在荷马名下的系列圣诗也开始在希腊世界流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与伯罗奔尼撒战后希腊世界形成的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阵营有关。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阵营有着明显的不同,城邦在建立过程中政治及文化认同感空前加强,在追求城邦阵营共同性基础上对各自城邦的特点也尤为重视。每个城邦将自己城邦的建立与史诗描述联系起来,从荷马史诗中寻找城邦建立的证据,有的城邦还把荷马史诗看作是本邦的文化遗产,对史诗文本进行修订。后世多个版本如雅典所认可的庇西斯特拉图斯本和斯巴达所认可的吕库古编订本[9],都是在这一时期衍生出来的。对荷马史诗认识的多样性和多个版本的出现,既为后世学者的研究设置了障碍,也提供了多种文本的参照。 早期荷马研究多围绕史诗的修订而展开。希腊化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对荷马史诗从语文学角度进行了系统考证,就今天所见到的资料来看,《伊利亚特》《奥德赛》的许多段落都是当时学者修订的。普鲁塔克认为,亚历山大在远征东方时随身携带着他所喜欢的荷马史诗,很有可能就是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藏书甚至修订本。这个本子与较早在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所出现的本子有何关系,至今仍不得而知,但是凭借亚历山大与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密切关系而言,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定本校订过程中参考这个由亚里士多德所修订的本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一直沿用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者萨摩斯瑞斯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根据雅典手抄本所修订的版本肯定集合了古代多个修订本的优点,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抄本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订本也必然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藏本的重要参考[10]742-744,759-761。除了萨摩斯瑞斯的阿里斯塔库斯,其他希腊化时期的学者肯定也为史诗校勘付出了巨大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上下文意思拟补阙文部分。正是这些由学者自行添加的阙文给后世研究带来了很大麻烦,原因在于学者在拟补阙文的时候没有在相关地方做必要的说明,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辨别哪些是原有的段落,哪些是学者的师心自用。 格拉古兄弟统治时期,古典学术研究在罗马兴起,卡里马库斯命令学者彻底搜索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之后所完成的著作[11]13。经过瓦罗(Varro)的努力,到罗马帝国早期,希腊的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蜂拥来到罗马。到公元3世纪,希腊文化中心从盛极一时的亚历山大里亚迁移到罗马。在漫长的中世纪,荷马研究也逐渐走入沉寂,仿佛处在黑暗时代。直到文艺复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翻译、印刷荷马史诗,荷马史诗重又恢复生机。这一时期,修道院为荷马史诗的保存和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保存在修道院中的史诗文本因修士所依据的不同版本而呈现出多种形态[12]8。同时,修士在处理荷马史诗时的马虎态度为后来的研究增加了困难,与希腊化时期学者拟补史诗阙文不同的是,修士对后代学者的考验缘自其主观态度。但无论是因拟补阙文还是因修士马虎形成的问题都是荷马史诗流传过程中的版本问题,对文本的校勘一直是荷马研究绕不开的难题。后世学者的荷马研究主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研究史诗叙事技巧和考证荷马史事的可靠性。 17世纪90年代,随着理性时代的到来,科学领域的进步观念被移植到人文学科。英法学术界围绕《伊利亚特》《奥德赛》内容的古胜于今抑或今胜于昔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后来这场“古今之争”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论争中法国学者拉宾和英国学者坦普尔坚定地主张是庇西斯特拉图斯修订了史诗,他们相信荷马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并且相信荷马有着渊博的关于当时社会的知识[13]416。还有一批学者则试图对荷马的无所不知提出怀疑。英国剑桥大学的理查德·本特利在回应安东尼·考林斯[14](Anthony Collins)的文章中表示,他不同意考林斯对于包括荷马在内的古代知识完美性的论述,荷马史诗在许多方面都是矛盾的。对荷马史诗表现出的取悦和感动观众的特点,本特利认为:“在那样一个时代和环境中荷马不可能有那样的雄心抱负。”[15]正是本特利的这篇文章重新开启了“荷马问题”的讨论,让近代以来的学者重又把目光聚焦于荷马这一古老的话题。本特利不仅对亚历山大里亚学术提出挑战,质疑荷马知识的准确性,而且在具体研究中推动了荷马研究,例如对古希腊字母“双伽马”(Digamma)的探讨超越了亚历山大学者对前伊奥尼亚早期字母体系的认识。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者已找到史诗并非一人所作的证据。至于史诗文本的最终形成,学者们仍坚持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斯父子编撰的说法。 参与“古今之争”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史诗文本前后矛盾、叙事脱节的现象。现代古典语文学创始人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1795年为《伊利亚特》所写的序言《荷马导论》[16]3-35中认为,前后矛盾以及叙事不连贯的脱节现象是史诗口头传播中不可避免的,传世的荷马文本并非全由口头创作而来,而是经较晚出现的书写加工过的。沃尔夫进一步推断,《伊利亚特》至少由两位作者整理而来,荷马只是第一位相信特洛伊故事真实性的诗人的名字,抑或是一个教师兼歌者的名字。荷马史诗虽以口头传播,但经由作者整理后已与传统书籍区别不大,最后呈现的文本都是作者以手拿笔书写出来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荷马史诗的创作形式,沃尔夫主张对《伊利亚特》及《奥德赛》进行文学的批评,通过“解析”文本的演进过程找出真正的“荷马”。沃尔夫的研究影响了19世纪后继的荷马研究者,学者们以文本中出现的不同方言作为切入点,对史诗所呈现出的伊奥尼亚方言、阿提卡方言和艾奥尼亚方言混用现象进行专门讨论。荷马史诗内容主要采用伊奥尼亚方言,老的伊奥尼亚方言中与格复数以-οισι,-αισι,-ησι结尾,而晚出的方言则以-οιζ,-αιζ,-ηζ结尾,学者据此对史诗方言进行年代以及人物社会阶层的划分[17]9-10,从方言的先后顺序中“解析”文本演进的线索。然而,到19世纪30年代,支持《伊利亚特》及《奥德赛》由多位诗人整理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反对者认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在结构上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史诗里出现的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现象只是貌似如此而已。因此,围绕史诗的创作学界形成两个流派:“解析派”(Analysts)和“统合派”(Unitarians)。“解析派”因其研究方法而得名,“统合派”则以其学术观点被学界所熟知。“统合派”坚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虽不一定由同一位诗人整理,但却可以凭史诗在艺术上所表现出的高度“统一性”推测两部史诗分别由两位不同的诗人独立完成。 在19世纪荷马史诗创作方式的讨论中,“解析派”占据了古典语文学界的主导地位,但是在“解析派”内部也有分歧,存在着“短歌说”(Liedertheorie)和“核心说”(Uriliastheorie)两种不同的观点。“短歌说”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别是由很多不同的诗歌拼合而成的,几乎每一个场景就是一首口头诗歌。沃尔夫即持这一观点。“核心说”则认为,史诗的原型是原始的简单故事,后来随着传播过程的不断改编,相应的叙述附加物也不断融入原有的故事内核,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形成缀合效应。《伊利亚特》的故事原型即是“阿喀琉斯的愤怒”[18],特洛伊战争只是在这一主题下附加的内容罢了,故事成型以后,原来的“愤怒”也湮没在了精彩的故事叙述中,叙述过程中附属叙述取代主题叙述。附属叙述因其传奇色彩而在传播中被理想化,进而形成后世广为流传的史诗。于是,坚持“核心说”的学者也对史诗的艺术性产生怀疑,维拉莫维茨就曾感慨《伊利亚特》的创编者是“一个资质平庸、东拼西凑的诗人”[19]228。 在质疑声中,20世纪20年代的荷马研究“统合派”占据了上峰。学者们逐渐接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别由一位诗人(并非指同一位诗人)创作的观点。 二沃尔夫开创了荷马研究新“范式”,奠定了现代意义上古典语文学的基础,以沃尔夫为代表的“解析派”通过解析文本的演进过程来寻找真正的“荷马”,“统合派”则在与“解析派”的辩难中形成。两派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对待文本的态度却是一致的。“统合派”学者雷尔斯(Karl Lehrs)1831年在哥尼斯堡大学开设“荷马导论”课程的时候,试图通过分析《伊利亚特》不同卷次里有相互关联的章节,把不同部分串联起来,还原史诗的某种统一设计。在研究方法上,“解析派”和“统合派”都更倾向于语文学范畴下的文本解读。 我们在看待沃尔夫的古典学贡献时不应该忽视英国学者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的影响。伍德并非专门从事荷马研究的学者,他是一位旅行家。为了弄清楚荷马史诗所记载的故事是否是真实发生过的,伍德与伙伴来到小亚细亚和爱琴海沿岸进行实地考察。1767年,伍德回到英格兰以非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将自己考察期间有关史诗的想法刊行出来,后在1769年正式出版。伍德去世后,1775年他的著作再次出版,著作名字定为《荷马的天赋和书写:古代和现代部落的比较研究》[20]。伍德在第一章中即明确提出:荷马时代的诗人过着最为朴素的生活,通过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表达;当时虽然有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传统,叙事传统也已发达,但是人们却不知字母为何物,既不能读也不能写。那么,如此长篇幅的荷马诗歌何以能够从书写文字产生前的上古时期流传到文本确定的庇西斯特拉图斯父子时代呢?在没有书写文字作为辅助手段帮助记忆的情况下,诗人只能通过强行记忆的手段通过口头创作过程来进行。创作过程中诗人开始运用大量重复性的词句来减少记忆的工作量,多次重复朗朗上口的六部格韵律,观众也不会感到突兀和单调。诗人的记忆任务相对繁重,但是作为职业的吟唱诗人,与今天人们的记忆能力相比,他们根本不必为了繁琐的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去浪费记忆的潜力,他们的记忆工作相对单纯。伍德的著作在欧洲大陆有广泛的读者群,当沃尔夫读到伍德关于荷马的论述后,受到很大启发。就在沃尔夫读到伍德的著作后不久,1788年,法国学者魏劳伊宗(Jean-Baptiste-Gaspard d'Ansse de Villoison)刊布《伊利亚特》的威尼斯古抄本(Codex Venetus A)。威尼斯古抄本是现存最早的《伊利亚特》皮纸抄本,附带抄有亚历山大学者的旁注,这一版本的发现更加坚定了沃尔夫寻找真正荷马的决心。于是,1795年沃尔夫完成了为《伊利亚特》所写的序言《荷马导论》。 沃尔夫古典语文学的研究范式得益于口头创作理论,反过来又推动了口头创作理论的发展。沃尔夫古典语文学角度的荷马研究虽然立足于文本,却难以离开口头创作的传统,“诗歌拼合”“故事缀合”讨论的背景也都是口头创作传统。“统合派”甚至认为诗人荷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近乎完美的艺术是因为诗人正处于口头传统的最高水平。因此,在荷马研究中古典语文学的推进也会影响到史诗口传性质的探索。文本与口传两个层面研究的结合最终表现在对史诗重复出现的套语和大段诗句的讨论中。19世纪末,卡尔·施密特(Carl Eduard Schmidt)的《荷马字编》开始对荷马中重复出现的修饰短语进行系统整理,开启了专门研究荷马“程式”的新角度。法国语文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也认为史诗中重复出现的名词短语像是“程式的设计”,并且认为,这些名词短语可能在荷马之前就存在,只是尚未遵循六音步韵律的规则,步格还较为灵活,不那么严格[21]61。1870年以后考古学的发现也在证明荷马史诗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随着阿提卡考古发掘学者们注意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所刻铭文仍与公元前8世纪用同样的字体,说明希腊字母是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才得以普及[22]5。考古学的证据有力地证明,荷马研究从文本解放出来是必要的。 1928年,帕里在巴黎出版他的博士论文[23],认为这种套语和其中不规则的现象都可归于口头传统,是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帕里认识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通篇都在运用套语。他进一步统计出英雄、神、事物和地点的所用的各类谚语,从而分析出六部格韵律的固定“程式”。帕里对荷马“语言的艺术”的论证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后,他将研究进一步转向南斯拉夫民间诗歌。帕里试图从南斯拉夫英雄诗歌的表演现场找到荷马史诗的原型,来验证自己有关荷马史诗采用六部格韵律的理论假设。他随机找到几个案例——如穆尔库和格斯曼关于南斯拉夫诗歌的论析,又如拉德洛夫关于吉尔吉斯-鞑靼诗歌的探讨—并对这些案例以荷马风格的特征为依据进行逻辑推演。在比较研究后,他在其田野笔记《科尔·胡索》中写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我所获得的各类口头诗歌的信息而言,南斯拉夫似乎是我心目中最为合适的研究对象了。对依然处于活态的口头史诗提出见解,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如果我还想对我的荷马研究有所肯定的话。”[24]72帕里从1933年夏季开始前往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到1934年6月进入系统搜集材料阶段,一直到1935年9月结束,历时16个月。随同他一起考察的还有他的学生兼助手艾伯特·洛德。他们搜集了来自穆斯林传统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平均篇幅明显长于当地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诗歌。帕里认为,这些诗歌不仅在篇幅长度上,在风格的成熟度等方面都接近荷马,从而为他在博士论文中将“程式”套语归于口头传统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帕里的“口头诗歌理论”并未引起荷马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英国古典学家莫里斯·鲍拉(Maurice Bowra)在1930年著作《〈伊利亚特〉中的传统和构思》[25]中还根本不曾提及帕里,而到1952年其著作《荷马式的英雄诗》[26]出版时开始对帕里的研究进行讨论。帕里去世后他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帕里的助手洛德接着这一课题继续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口头诗人和书写诗人创作的性质及其关系。1960年,《故事的歌手》出版,“帕里-洛德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被系统整理出来,荷马史诗隶属于口头传统的观点得到进一步论证。对于帕里首先提出的“程式理论”,英国学者韦德-格瑞(H. T. Wade-Gery)曾给予高度评价:“对于传统荷马研究,近些年来最为严厉的打击来自帕里的著作,帕里可称得上是荷马研究的达尔文。达尔文将创造了世界和人的神的手指从其身上移开,帕里看上去是将创造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诗人荷马从著作中移开。”[27]38-39 1979年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的《最好的阿凯亚人:古风希腊时代的英雄观》认为,史诗开篇呼求缪斯即是诗人的一种表演[28]48。1996年纳吉的《荷马诸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表演文化,由此也还原出荷马史诗的形成过程。认为现存的24卷《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太可能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写下来的,当时希腊字母还未成熟,尚处于婴儿期,史诗传播仍以表演形式进行,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创作。荷马在创编、表演和流传过程中,史诗按照其固有的表演形式进行,文本的变化越来越小,逐渐走向固定。文本相对稳定的阶段可以归结为史诗的吟诵时代[29]149。另一个与吟诵文化相关的名词——“歌吟文化”(song culture)由美国学者赫林顿(John Herrington)提出。据他考察,公元前400年以前希腊歌吟文化已经十分流行,当时已有17个戏剧表演场所,而戏剧表演的最初形态与此前的诗歌吟唱传统密切相关,在希腊古风社会最为重要的情感和思想的表达媒介是歌声[30]3-5,160-166。默瑞(Penelope Murray)和威尔森(Peter Wilson)的 《音乐和缪斯们:古典雅典城邦里的mousikē文化》是一部全面研究古典城邦文化的著作,对处于希腊文化核心的mousikē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含义比英语的“音乐”更广泛,代表了更加广泛的文化。mousikē作为一种最为普通的形式代表了希腊人密切结合了音乐、歌词和舞蹈,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表演,从私人住宅中的小规模娱乐活动到精心策划的整个城市节日。此外,mousikē还是连接城邦过去和现在的活的媒介,在希腊宗教中处于核心地位,占据了希腊教育的重要比例[31]1-4。杰拉尔德·埃尔斯(Gerald Else)对史诗在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考证,认为后来的悲剧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来自宗教仪式和史诗表演[32],从而对史诗的表演特征做出明确解释。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认为表演是古代城邦生活的一部分,公民通过参加活动提高城邦的凝聚力,诗歌表演是古代文化的社会基础。他不但有着严格的学术论证,而且将史诗表演推广到现在的舞台,以表演的形式推广古典史诗表演艺术[33]。 三帕里和洛德以活态的“口头传统”印证了荷马史诗的真实性,为荷马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实质上,打开通往“真正的荷马”大门的钥匙是早期希腊“口头传统”中的表演文化。对于文本创作环境的讨论成为后世学者重要的研究课题,诗歌的表演场景是近几十年来学界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34]348。“表演中的创作”“诗即是歌”“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创作”等观点逐渐被学界所接受,源于“荷马问题”的“口头传统”理论被应用于其他希腊早期诗歌的研究。 当传统的语文学无力回答荷马和梭伦诗歌研究的难题时,文化人类学作为古典学的辅助手段显示出强劲的力量。荷马研究中“口头传统”的发展尤其是帕里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的提出,打破了19世纪以来单一语文学方面的考证困局,学术讨论向多学科融合发展。经过摩尔根、库朗热、韦尔南、戴地安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古代社会结构的人类学解释已经趋于成熟,这也促进了传统语文学与古典学的结合。1888年,英国学者泰勒发表了一系列“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篇章的人类学解释”的讲座,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人类学融入古典学研究中来。学科融合为古典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长期困扰学界的“荷马问题”逐渐在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中找到答案。荷马史诗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标准的版本,在创编、表演和流传过程中荷马故事逐渐确立下来,在这一过程中早期希腊社会的表演传统起到重要作用,按照固有的表演形式对史诗进行重复的演绎,每一次表演就是一次创作,随着文字的普及,文本才最终固定下来。 “口头传统”理论之所以能够较合理地解释“荷马问题”原因有二。第一,“口头传统”理论还原了作品的表演场景,找到了荷马史诗的创作语境,从历史角度对作品创编和流传进行解读。第二,“口头传统”理论下的历史解释跳出了语文学考证的局限,把历史作品放置到更为丰富的希腊早期文化大背景下,赋予作品以新的解释内涵。这种突破可以从维柯《新科学》中找到最早的源头,维柯认为荷马史诗的语言虽然粗俗,所描写的战争虽然十分残酷,但是这种武力至上的“正义”恰是当时英雄时代希腊人的真实认识。荒诞不经的神话和传说,在维柯看来是经岁月变迁所掩盖了的语言和社会习俗。维柯找到了解读古代希腊人情感和民俗的较为合理的方法,他将史诗的口头创作与文本化过程看成是两个截然分开的过程。维柯试图在人类社会中建立“新科学”的主张跳出了语文学考证的局限,将研究重心放到史诗和诗歌所产生的早期希腊文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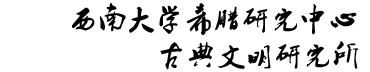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