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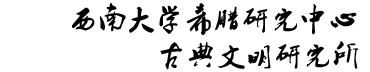
| 《传道书》的正义与施特劳斯的回归 (王献华) |
| (发布日期: 2017-06-11 13:47:15 阅读:次) |
《古典学评论》第2辑 《传道书》的正义与施特劳斯的回归*
王献华
摘要: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芝加哥大学希勒尔学院(Hillel House)的演讲以“进步还是回归:西方文明当前的危机”为题,但基于文本的重读和分析能够看出,施特劳斯在演讲中所号召的“回归”更多地是指现代犹太人向犹太教的回归,而无法解读为普遍意义上现代向古代或者古典的回归。换句话说,除了现代犹太人向犹太教的回归或者“改悔”,文本中看不出施特劳斯所谓回归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没有在时间意义上明确地向古代或者古典回归的指向。通过对希伯来圣经中《传道书》体现出来的正义观念的整理,更能够看出施特劳斯所说的犹太教也是一种特定传统的犹太教,和古代的希伯来宗教颇不相同。向犹太教的回归在此意义上也同样没有回归古代的意思。 关键词:施特劳斯,《传道书》,“回归”,正义
1952年11月,施特劳斯受邀在芝加哥大学希勒尔学院(Hillel House)以“进步还是回归:西方文明当前的危机(Progress or Return?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为题做了三次演讲,但讲稿到近三十年后才在达特茅斯学院马斯特斯(Roger Masters)的帮助下发表,这时施特劳斯也已经去世多年了。[1]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其回归古典哲学的药方早有中外学者加以讨论,[2]他并举所谓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国思想者的注意。[3]只是本文作者学力有限,无力对施特劳斯思想进行系统的阐发,也无法在具体问题上做到足够深入。本文以“进步与回归”一文为基本阅读对象,基于对《圣经》文本传统中的《传道书》的一点认识,试图理解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和他所说的回归,对他在此语境中对希腊特别是希伯来传统的处理方式稍作检讨。[4] 一、施特劳斯的“西方”危机施特劳斯的演讲开宗明义:“我们演讲的题目昭示着进步已经成为问题,看起来它已经把我们带到了深渊边缘,因此必须考虑不同的选择。”危机已经出现,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施特劳斯提出“回归”的问题。施特劳斯的“回归”应该用着重号或者要加上大写,因为它并非一般的回归,而是“悔改(Repentance)”,是救赎意义上的回归。他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他所说的回归确实是悔改和救赎,是遵从先祖的召唤回归先祖所理解的原初和开始的地方。 开始并不一定和未来冲突,因为对未来的渴望正是要回到开端。在近现代的语境中,回归还有犹太人回归犹太教的意思。正是进步的理念让近代犹太人选择背弃犹太教。通过对斯宾诺莎的分析,并回顾整个近现代犹太人运动的波澜,施特劳斯认为近现代的“犹太人问题”无非一场巨大的悲剧。犹太人基于进步的理念选择背教,进步的理念却不但没有说明这种选择的正确,反而以悲剧性的方式地昭示出这种选择的错误。近现代犹太人的命运揭示和体现着进步理念的危机,而进步的理念正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如果说回归是回到过去,进步则把目标设定在不确定而且开放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中的进步含有一种和手工艺的类比,因此将社会的进步和智力的提高相提并论。这种不加限定的进步不考虑宇宙灭绝事件可能造成的终结,承认起点却不在乎终点,而且认为人类一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可逆的。在这样的进步观念支配下,现代人如同双目失明的巨人,能够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缺乏智慧和善的导引,横冲直撞却不知去向何方。[5] 现代人用进步和反动的标准取代善恶,典型的体现便是所谓对历史的发现。对历史的发现让现代犹太人在抛弃了传统之后无家可归,但所谓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现代人用历史意义上的过去和未来替换了永恒,犹太人不过是适逢其会。施特劳斯将西方文明的整体性危机成为现代性危机,其核心就在于进步的观念。 要分析和应对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危机就要从西方文明的根基开始,也就是从《圣经》和希腊哲学开始。现代人基于进步的理念对二者加以取舍,但正如尼采所说,《圣经》体现的伦理信仰和希腊哲学的理性科学无法相互取代,而近现代发生的事件足以表明所谓现代科学精神的虚妄和危险。[6]现代人赖以自立的“历史的进程”导致了世界的野蛮化,却无法提供有效的理据来捍卫文明。十七世纪以来若隐若现的“古今之争”已经揭示出一些更为具体的现代性病症:哲学成为心理学,自由取代了美德,历史的发现让人们忘记了自己的限度。现代性的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性的病症,进步的理念制造了进步的陷阱,要重新取得西方文明在现代之前具有的尊严,就只能考虑回归。但西方文明有两处根基,该向何处回归,雅典还是耶路撒冷?“希腊哲学追求的是生命的自我理解,《圣经》所说的却是生存的虔敬。”试图调和这两种传统的努力只能够是努力,除非从根基上牺牲一端,二者之间的冲突无法消解。 施特劳斯并没有试图调和这两种传统,他认为两种传统的冲突恰恰也预设着某种一致,因为任何冲突都预设某种一致,正如人们如果不一致认可某件事物的重要也就不会有意见冲突。他强调这是比简单的形式上的一致更深刻的一致。就希腊哲学和《圣经》传统而言,施特劳斯认为在对道德的强调、道德的内容,以及对道德无法自足这一点的理解上都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在那个支持(supplement)或者成就(complete)道德的地方。[7] 希腊哲学和《圣经》传统应该说都是男性中心的,但它们都没有把男性气概或者勇敢当作最重要的美德,而是将最高的德性赋予正义(justice)。更为重要的是,希腊哲学和《圣经》传统都主要地把正义理解为对律法的遵守,不是对民法、刑法、宪法的遵守,而是对道德和宗教律法的遵守。在这方面柏拉图和《圣经》有着极高的一致性。根据这样的认识,施特劳斯将他对道德的讨论聚焦到正义问题上,因为神圣律法无论在希腊哲学中还是在《圣经》中都是正义的基础。问题在于希腊哲学和《圣经》传统中的神圣律法并不一样,而且是针锋相对的。希腊哲学的神圣律法基于“自然”观念,依赖在自然观念的的前提下的人的认识,而《圣经》传统的神圣律法来自具有人格的上帝,依赖对上帝恩典的信仰。所以希腊道德包含人的“豁达(magnanimity)”而希伯来道德排斥人的骄傲。施特劳斯说,后一种态度更能强化道德律令。[8] 希伯来人全能的上帝观念和希腊哲学的“自然”观念是二者根本的差异所在,也是简单地强调二者的类似之处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施特劳斯试图在前哲学的层次上给出解释:“如果我们假定‘道(way)’的概念确实相当于前哲学中的(prephilosophical)自然,我们也就立刻能做出这样的观察:在很多的道中有一种道特别地重要,那就是我们所属人群的道,‘我们的道(our way)’。”[9]祖先之道成为神圣律法(theos nomos)再自然不过,希腊哲学和《圣经》传统在何为神圣律法上的差异出自二者祖先之道的不同,只不过说明神圣律法可以有多种样式。我们固然要独立地认识宇宙,对不同的祖先之道有所判断,要清楚祖先之道和良善之道的不同,求知的基本态度恰恰在于认识到道之谓道自非人力所及,可见的宇宙未必依赖人的思想。 希腊哲学在追问的过程中取消了神,《圣经》却坚持以全能上帝为核心的神圣律法为排他的唯一,这样的结果有些不幸。但《圣经》传统更清晰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上帝必须有意志,无法在希腊意义上为人所知,而信仰和神圣律法只能建立在他的圣约之上。施特劳斯注意到,“非同寻常的事实在于,如果更仔细地既研究希腊哲学家也研究《圣经》,人们会发现在两种西方思想的根基之中都能够看到可能的不同选择何在,也就是神性。”[10]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让我们不断地追问,《圣经》传统提醒我们,知识只有奉献给神才是道德的和必要的。二者冲突无法消解也没必要消解,因为它可能正是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所在。这让人欣慰的说法有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以这种冲突生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应该在这两种可能中做出选择,或者做个直面神学挑战的哲学家,或者做个直面哲学挑战的神学家。”[11] 真正重要的是作为哲学家需要保持对古典问题的追问,这也是施特劳斯强调回归的真正意图。但他不是要回到古代或者在古人的思想中选择正确的结论,只是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古人面临的问题,而且要知道它们并没有得到解决。应该说在前两讲中施特劳斯已经把他的基本思路说清楚了,所以除了总结已经说过的内容,在最后一讲中施特劳斯只是选择性地重述和强调了部分内容。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对自己思路的澄清,他特别提起现代历史观念,说“我们现在的类似概念,比如加大写的历史,是非常晚的概念也是衍生出来的概念,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让它无力解说早期思想。早期思想来自传统的创生时期,并不是衍生出来的。”[12] 施特劳斯承认,其实是历史的观察让他看到了希腊哲学和《圣经》传统的差异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但他暂时不想试图证明为何祖先之道便是良善之道。只是他意识到,《圣经》传统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冲突触及人类面临的基本冲突,也就是思想和行动或者语言与作为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希腊哲学执着于思想,而《圣经》传统以作为为先。[13]现代人往往将某种哲学体系误认为哲学本身,但哲学思考并不会因为某种完整的哲学体系的存在而罔顾这样的根本冲突。也是在这个层面上,现代人的哲学也无法成功地取消启示的可能性,因为现代哲学并无法认识“全体(whole)”,也就无法真正认识人并明了人应有的生存。 现代哲学以论证上帝存在与否的方式谈论启示根本就谈不上“取消”,因为启示根本就不在哲学理性范围之内,它是“超理性(suprarational)”的。另外一种对启示可能的挑战方式,更为典型地体现在现代历史学之中,是指出例如上帝的作为之不可能,或者和上帝的属性冲突,但这种思路的根基实在是一种自然神学。所有对启示的反驳都已经预设对启示的拒绝,而所有对哲学的反驳都已经预设对启示的信仰,选择哲学的生活并接受二者的冲突便是面对危机的一种可行选择,至少是一种“非悲剧”的选择。[14] 二、“回归”问题和时间的方向布拉格曾经指出施特劳斯所谓的“雅典和耶路撒冷”问题背后其实还有“麦加”。[15]祖科特也强调施特劳斯和麦蒙尼德以及通过麦蒙尼德和阿拉伯思想之间的关联,认为在关于理性和信仰的问题上,施特劳斯的立场可以说是麦蒙尼德的镜像,在对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往往是对麦蒙尼德立场的继承或者映射。祖科特认为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大概是施特劳斯的哲学面向的主要是非犹太人而麦蒙尼德则为犹太人写作。[16]不过,根据施特劳斯本人提供的线索,通过辨析内容的异同和语境的差别来了解他的思想渊源,他对中世纪犹太阿拉伯传统的重视和继承,并不能真正解读施特劳斯所说的回归。 施特劳斯不认可现代人对古人思考的问题采取的取消与否认态度,不认可现代人自己的提问方式,采取中世纪的思想资源来表述自己的立场,但这种思想资源的选择很难说是他的回归真正的指向,二者需要分别开来对待。祖科特特别注意到施特劳斯并没有明确地要回归中世纪犹太或伊斯兰传统,甚或古典时代的政治哲学。[17]施特劳斯强调哲学作为生存方式的自觉选择,表面上看是回归麦蒙尼德甚至回归苏格拉底,但他在题目中特别拿来和进步对应的“回归”,无法在历史意义上作为进步的反义词来理解。他的出发点是现代进步观念及其体现的现代性危机,但他的回归绝不便是回到过去的哪个时代。 上文已经提起,施特劳斯开篇所用的希伯来语“回归”一词更重要的意思是悔改而不是向古老时代的回归,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虽然提到《圣经》将救赎等同于复原,将目的等同于开端的传统,给出了救赎意义上的回归的原始语境,却没有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没有对这一语境本身的适用性进行讨论,只是转而解释现代犹太教语境中向传统的回归概念。施特劳斯所用的“回归”概念至少不够明确,需要做进一步的辨析。施特劳斯列举的“回归”概念的语境具体而言有两种,二者都是广义上犹太传统的:《圣经》语境和现代犹太教的语境。 《圣经》时代的古代西亚和地中海东岸语言中表示时间的词语一般借自表示东西方位的词语,本意往往来自日出日落的生活经验,表达时间上未来的词语恰恰来自表示空间上的后方,所以有学者形象地说他们似乎将人生理解作在时间流之中背朝未来地倒退。[18]古埃及表示时间上的以前(hnt)来自表示空间上的南方一词,也遵循类似的逻辑,因为尼罗河上游或者日出的方位对埃及人来说在南方。[19]这样或者可以理解《圣经》对过往的执着,希伯来语没有和“进步”相对应的词语,并不让人惊讶。[20]这些古老的传统真正揭示出来的问题在于,引入时间流的方向来理解施特劳斯所说的进步和回归问题,强加给施特劳斯一个心目中属于过去的黄金时代完全没有必要。 自然,回归概念不必要以时间的方向来解释,并不意味着时间问题不需要讨论。一般认为,《圣经》传统中的时间观念主要是目的论的,而希腊古典时间则是循环论的。但根据学者的研究,《圣经》文本中,如果说后文要涉及的《传道书》因为篇幅不大而且有希腊影响的嫌疑而不足为据的话,《士师记》等作品表现出足够明显的循环论倾向。根据这样的理解,从创世到救赎也可以看做不过是一个更高的轮回。将《圣经》时间用末世论来解释主要地是基督教传统对《圣经》传统有意无意的误读,得不到足够有效的文本证据支持。《圣经》的循环论并不一定和末世论相冲突,因为二者的差别只是在于后者预设时间有终点,前者虽然有以起初为未来的观念,却并不明确是否救赎便是时间的终结。 如果说《圣经》传统有末世论的话,它不是严格的线性时间观念,在线性时间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强加给它一个终点其实是一种扭曲。[21]施特劳斯注意到《圣经》传统将未来看作回归,并指出现代进步观念中的时间只有起点而没有明确的终点,但他不明言《圣经》时间原本也没有时间意义上的终点。《圣经》追求复归创世秩序,如果成功复归了创世秩序,时间也并没有结束,关于后者的预设来自其他地方。 施特劳斯的“回归”虽然引自《圣经》,但《圣经》传统至少在对时间的理解上形不成和进步观念的对立,反而和进步观念中时间有起点却没有明确的结束的认识并不冲突。根据弗格森的看法,进步的观念也说不上是现代性的特征,西方现代性的进步观念更很难说来自施特劳斯所批评的工艺类比,反而更可能来自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这恰恰并不来自于什么现代才有的偏见。[22]施特劳斯所说的回归既不是在线性时间意义上向着现代人所谓未来的相反方向的回归,也形不成对现代进步观念隐含的时间观的否认,现代进步观念更未必和《圣经》时间观念形成真正的差异。 施特劳斯的回归很难依据他所引用的《圣经》语境来理解,甚至很难用圣经意义的“悔改”来理解。在她对施特劳斯的回归进行解释的文章中,祖科特将施特劳斯的问题转化为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不是会更好的问题,但没有明言究竟说的是何时何地何人的世界。[23]考虑到施特劳斯的回归概念如果并非真正来自《圣经》语境,很自然的理解就是他所说的回归真正的语境其实是他提到的另外一个语境。施特劳斯把现代犹太教中的回归问题的根源也当成现代进步观念的后果,当成犹太人受其蛊惑而出现的迷途。根据以上的认识,假如施特劳斯心目中犹太教的传统等于就是《圣经》的传统,那便很难说这种迷途意味着对犹太教的背叛。施特劳斯心目中的犹太教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却意味深长。 一种合理的思路是,施特劳斯把现代犹太教的问题提升到了现代性问题来处理,或者说他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是现代犹太教的问题。虽然施特劳斯继承麦蒙尼德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自觉的选择了哲学家的角色,他的回归概念却只是在现代犹太人回归犹太教的具体语境之中才有具体所指。麦蒙尼德所处的欧洲中世纪固然没有施特劳斯所说的现代性危机,却存在更为具体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冲突。施特劳斯上溯到苏格拉底来作为他的思想渊源,只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真正关心的回归问题只是犹太人回归犹太教的问题,甚至并不在乎所回归的犹太教究竟是什么内容。一个选择哲学生活直面神学挑战的思想者,一个追问终极价值的研究者,自然要直面现代性的危机,却并不真正有必要用回归来作为对可能方案的描述。之所以如此修辞,只是因为心有所系罢了。[24] 这是个典型的现代语境中的问题,而且施特劳斯对它的关注方式也是现代的。来自外部对施特劳斯的批评之外,施派内部对所谓雅典和耶路撒冷问题也有不少争论,各执一词强调施特劳斯思想的宗教性或者哲学性,却倾向于一致否认施特劳斯思想的政治指向性。[25]然而至少从正统意义上说,传统犹太教缺乏对现实政治的热切关心。[26]如果我们理解不错的话,施特劳斯用回归的旗帜对现代犹太教问题所做的干预,实在并不能用宗教性或者哲学性来解释,只能理解为有意识的政治指向。施特劳斯受到以麦蒙尼德为代表的犹太传统思想家的影响,[27]但他号召复兴希腊古典政治哲学的态度背后是其非常鲜明的现代犹太人身份。[28] 三、“正义”和《传道书》的快乐主义在《圣经》各卷中,对《传道书》的解读犹为人言人殊,包括应该放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中来解读它。[29]《传道书》也是整个《圣经》中明确地对时间问题有所思考的书卷。但本文这里将《传道书》专门提出来讨论的原因首先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正义的问题。施特劳斯将希腊哲学的正义观和希伯来圣经的正义观进行对照,强调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在根本问题上的差异,将二者的差异当作具有根本性的思想问题对待,并进而和西方文明的根基建立关联,是极为强势的逻辑预设,并不一定合理。正如希腊哲学并非铁板一块,希伯来圣经中的正义观也相当复杂,将二者某个方面的差异用雅典和耶路撒冷背后的宗教思想传统作为标签来加以讨论,这样做的必要性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施特劳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亚伯(Abel)和该隐(Cain)的故事,一次是说并非体现文明的农夫该隐而是文明之外的牧人亚伯在圣经的上帝眼中更受青睐,另一次是在谈到圣经中对定居文明的态度时再次以该隐为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创世纪》的故事情节,是该隐的子孙而不是亚伯的子孙构成了后世的以色列人。《圣经》对定居文明态度的晦涩并不意味着对自身传统的不同定位。而且在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中,上帝并没有因为该隐杀死亚伯而杀死该隐,经文只说给了该隐一个意味深长的印记('th)。[30]根据莫布利的研究,所谓该隐的印记很可能是指上帝赠与该隐的话“Therefore, whoever kills Cain will suffer sevenfold vengeance”。[31]更有意思的是,亚伯的名字和《传道书》中最为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一般译作“虚空”的正是同一个词。[32] 如果将《创世纪》的亚伯和《传道书》的HBL联系起来,对后者“虚空”的译法就是不成立的。道理很简单,这个亚伯他虽然死了,但是他毕竟活过。正是这个 “亚伯”一词,体现了《传道书》的世界观,体现了《传道书》对所处世界的基本认识。[33]另一方面,根据姚司马(Tzemah Yoreh)的看法,《传道书》要表达的立场并不在它的起首句体现出来的世界观,而是在它“玲珑结构”的文本中心句,其内容是一种快乐主义(Ecc. 5:18)。[34]这种快乐主义的态度常见于古代近东文学,应该认为是古老的近东智慧传统的一部分,泛泛而言的话也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常见的一种人生态度。[35]快乐主义并不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它只是面对世界时采取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背后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思想内容才是真正将《传道书》区别开来的部分。 在快乐主义的态度背后,《传道书》思想内容的核心关怀正是正义问题,而对正义问题的认识基于“亚伯”的世界观。传统看法根据《传道书》起首提供的信息认为《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在圣经传统中是智慧之王,这符合现代人们对《传道书》内容的一般接受方式。但是就古代近东而言,智慧之王和正义之王原本便很难区分,将所罗门王当作现代人心目中的智慧之王只怕是一种误读。[36]至少根据一种看法,《传道书》的内容甚至可以认为是对《士师记》中复杂的政治形态的评论和总结。[37]尽管采取的语言方式仍然继承所谓的智慧文学传统,《传道书》的文本中大量章节对正义问题的讨论足以佐证其核心关怀所在(Ecc. 3:15-17; 4:1; 5:7; 5:16-18; 7:14-16; 8:3; 9:1-2; 12:9-10),犹太解经传统也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38] 正是对正义问题的困惑让《传道书》决定通过研究检验生存,[39]在人生取向上的快乐主义恰恰建立在对正义问题上的悲观主义认识上。[40]只是这种认识上的悲观主义应该是罗姆克(Loemker)的第三种悲观主义,即历史的悲观主义。[41]这不是一种哲学,更不是施特劳斯一再批评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只是基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和总结。[42]在《传道书》的作者看来,如果用正义的尺度来衡量,上帝创造的一切实在“荒唐”。[43]“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去除不同的创造论背景,《红楼梦》第八回的这首诗或者能大体体现《传道书》的结论。 《传道书》的快乐主义态度与其说是对抽象的果报原则的造反,不如说是在研究的发现与传统的正义观念发生冲突时产生的知识上的应对,因此充满自我怀疑式的悖论和矛盾。但真正重要的是,《传道书》的探索并没有完全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认的泥潭,快乐主义的人生取向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取消,恰恰意味着对争议问题的探索在产生着实在的意义。《传道书》结尾回归正统信仰的部分是原始文本的一部分,还是后来虔敬的编订者有意的增补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44]技术上的讨论之外,回归正统信仰的内容实在不符合《传道书》整体上的思想逻辑。[45]很简单,如果正义问题可以取消的话,《传道书》整个的探究和若隐若现的快乐主义态度就都是没有必要的了。但《传道书》的存在便可以说明,《圣经》传统至少包含着对绝对全能上帝的质疑,包含着人们探索正义问题的可能性。 关于《传道书》的正义论,自然会有不同的分析,笔者倾向于认为其接近于现代正义论中的协商正义。[46]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施特劳斯对《传道书》体现出来的《圣经》传统的自我怀疑几乎完全采取忽略的态度,虽然提到《圣经》对正义问题的认识并不必然不能容纳自然正义的思路,却选择将《圣经》传统解读为一切以全能上帝为前提。这种绝对化《圣经》传统的做法,对于解读《传道书》来说,意味着取消其存在价值或者放任其快乐主义的解决方案;对于理解《圣经》传统来说,或者《圣经》只是施特劳斯的圣经,甚至不是古代希伯来人的《圣经》,或者施特劳斯拿来和雅典并举的并非无形的传统而是有形的政治,也就是耶路撒冷作为政治实体的认证。 余论:历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用研究历史的方式追问命运,和历史主义的历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只是将历史当作一个认知世界的领域,因此观察和体会历史上的事物以回观自身的命运,后者则以理性的名义追寻历史的规律,而且在近代欧洲并不成熟的历史主义版本中用起源替代创世,保留了太多基督教的背景。[47]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历史学的批评固然有其针对性,其中偏见也毋庸讳言。[48]施特劳斯本人恰恰有着强烈的历史关怀。这可能是施特劳斯的“隐晦教诲”的病源所在,也让人怀疑他这种有意的忽略是否有着其他的动机。 真正的历史学立足之处如果不是柏拉图文本中的理念,更不是施特劳斯批判的社会科学,而是人之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必然的自省行为,对这种自省的类型和它在人类社群生活中作用方式的研究或者就是历史学者真正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在施特劳斯的讨论中随时都能够体现出来。[49]施特劳斯正确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是现代世界之中的人们无法回避的。他没有明确地点明这也恰恰是史学的经典目标,反而将历史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不足等同加以批判。但这并没有取消古典学作为历史学的基本性质,史学古典学的目的正是对古典政治哲学问题的重新思考。[50]以传世古典作品的体裁来定义古典学难免因为丧失语境而影响对古典政治哲学问题的理解,而以民族或者文化为单位来划分中外无非重复施特劳斯的老路,无法去除以现代的民族政治指向偷换人类共同追问之讥。[51]
(作者简介:王献华,197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本文是2013年12月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暨“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主题发言,会后大略整体成文。由于笔者对施特劳斯研究颇为陌生,用意也更多在勾勒思路,文中表述不确之处必然所在多有,文责自负之外甚望同仁指教,必有助于笔者的进一步研究。笔者希望在此感谢甘阳、刘小枫先生的邀请和张文涛兄的盛情招待。 [1] 分别见Leo Strauss,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The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3 (1979), 111-118; Leo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Modern Judaism 1 (1981), 17-45. [2] Catherine H. Zuckert, "Strauss's Return to Premodern Thought", in Steven B. Smit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o Strau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3-118;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如杨适,"关于原创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考",《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杨适,"原创文化研究基本概念再探讨",《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4] 施特劳斯演讲的全文收入Thomas L. Pangle,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Leo Strauss: Essays and Lectur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及Kenneth Hart Green, ed.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 by Leo Straus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前者有中译本[美]潘戈,《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本文使用Green的版本即Leo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in Kenneth Hart Green,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87-136,必要时参考潘戈版及其中译。引文不加说明时为笔者自Green版译出。 [5]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p. 97-98. [6]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p. 98-100. [7]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p. 104-105. [8]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 109. [9]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 112. [10]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 115. [11]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 117. [12]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 118. [13]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 120. [14]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p. 131. [15] Rémi Brague, "Athens, Jerusalem, Mecca: Leo Strauss's "Muslim" Understanding of Greek Philosophy", Poetics Today 19:2 (1998), 235-259. [16] Zuckert, "Strauss's Return to Premodern Thought", p. 114. [17] Zuckert, "Strauss's Return to Premodern Thought", p. 117. [18] Silvia Kutscher and Daniel A. Werning, eds., On Ancient Grammars of Space: Linguistic Research on the Expression of Spatial Relations and Motion in Ancient Languages (Berlin: De Gruyter, 2014); Stefan M. Maul, "Walking Backwards into the Future: The Conception of Tim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T. Miller, Given World and Time: Temporalities in Context (Budapest, 2008), 15-24; Nicolas Wyatt, Space and Time in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Near East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1), pp. 35-36. [19] Wyatt, Space and Time in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Near East, p. 49. [20] 希伯来圣经《创世纪》首句通常译作“起初”的词语词根是常见的“头(r’s)”,和巴比伦的Enuma elish很可能是同一个意思,表示在空间概念上比人界更高的众神居住的天界。Green, ed.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 by Leo Strauss, p. 132. n. 6 [21] Marc Bretter, "Cyclical and Teleological Time in the Hebrew Bible", in Ralph M. Rosen, Time and Temporal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2004), 111-128. [22] Brett Bowden, The Empire of Civi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an Imperial Ide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48-49. [23] Zuckert, "Strauss's Return to Premodern Thought", pp. 110-111. [24] 此处可参见蔡锦昌,“以古贬今的政治社会思想史——李奥•史特劳斯<自然正义与历史>评述”,《东吴社会学报》第23期,2008年从中文语境对施特劳斯的评论。 [25] Peter Minowitz, Straussophobia: Defending Leo Strauss and Straussians against Shadia Drury and Other Accuser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9); Claes G. Ryn, A Common Human Ground: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Zuckert, "Straussians". [26] Hanina Ben-Menahem, "Is Talmudic Law a Religious Legal System? A Provis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24:2 (2008-2009), 379-401; David Novak, "Law: Religious or Secular?", Virginia Law Review 86:3 (2000), 569-596. [27] Kenneth Hart Green, "Editor's Introduction: Leo Strauss as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in Kenneth Hart Green,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 by Leo Straus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1-84. [28] Green, "Editor's Introduction: Leo Strauss as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Robert B. Pippin, "Being, Time, and Politics: The Strauss-Kojève Debate", in Robert B. Pippin, Idealism as Modernism: Hegelian Vari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3-261; Pippin, "The Modern World of Leo Strauss". [29] Yitzhak I. Broch, Koheleth: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 in Hebrew and English with a Talmudic-Midrashic Commentary (Jerusalem: Feldheim, 1982); David M. Carr,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48-455; Timothy L. Walton, "Experimenting with Qohelet: A Text-Linguistic Approach to Reading Qohelet as Discourse", (PhD dissertation, Vrije Universiteit, 2006). [30] James L. Kugel, Traditions of the Bible: A Guide to the Bible as it was at the Start of the Common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gina M. Schwartz, The Curse of Cain: The Violent Legacy of Monothe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31] R. W. L. Moberly, "The Mark of Cain - Revealed at Last?",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00:1 (2007), 11-28, pp. 14-15. [32] Jacques Ellul, Reason for Being: A Meditation on Ecclesiast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Michael V. Fox, "The Meaning of Hebel for Qohelet",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5 (1986), 409-427. [33] Carr,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A New Reconstruction很有意味地忽略了这个问题。William H. U. Anderson,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in a Genre Analysis of Qoheleth", Vetus Testamentum 48:3 (1998), 289-300; Katharine J. Dell, Interpreting Ecclesiastes: Readers Old and New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3). [34] Anderson,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in a Genre Analysis of Qoheleth"; Tzemah L. Yoreh, "Happiness, What is it Worth?", Beit Mikra 46 (2002), 353-370; Tzemah L. Yoreh, Ecclesiastes' Secret Symmetry, cited 06 Aug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biblecriticism.com/symmetrical_structures.html. [35] Bendt Alster, Wisdom in Ancient Sumer (Bethesda: CDL Press, 2005); Alhena Gadotti, ""Gilgameš, Enkidu and the Netherworld" and the Sumerian Gilgameš Cycle", (PhD disser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5), pp. 16-20; A. R.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36] Yee-Von Koh, Royal Autobiography in the Book of Qoheleth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6); Wilfred George Lambert, "Nebuchadnezzar King of Justice", Iraq 27 (1965), 1-11; Moshe Weinfeld,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The Expression and Its Meaning", in Henning Graf Reventlow and Yair Hoffman,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Biblical Themes and Their Influenc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2), 228-246. [37] William P. Brown, Ecclesiastes (Louisville: John Knox Press, 2000). [38] Broch, Koheleth: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 in Hebrew and English with a Talmudic-Midrashic Commentary, pp. 68-69, 77-79, 102-104, 114-115, 152-154, 190-191, 264-266. [39] Broch, Koheleth: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 in Hebrew and English with a Talmudic-Midrashic Commentary, pp. 114-115, 264-266; Pinhas Carny, "Theodicy in the Book of Qohelet", in Henning Graf Reventlow and Yair Hoffman,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Biblical Themes and Their Influenc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2), 71-81; Weinfeld,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The Expression and Its Meaning". [40] Mark R. Sneed, The Politics of Pessimism in Ecclesiastes: A Social-Science Perspectiv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2). [41] Anderson,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in a Genre Analysis of Qoheleth", p. 291; Jennie Barbour, The Story of Israel in the Book of Qohelet: Ecclesiastes as Cultural Mem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L. Loemker,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P. Edwards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114-121. [42] Green, "Editor's Introduction: Leo Strauss as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0:1 (1949), 30-50. [43] William H. U. Anderson, "Scepticism and Ironic Correlations in the Joy Statement of Qoheleth?",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lasgwo, 1997), pp. 4-26; Michael V. Fox, Qohelet and His Contradictions (Sheffield: Almond, 1989); Michael V. Fox,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Up: A Rereading of Ecclesiast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44] Eric S. Chrisitanson, Ecclesiastes through the Centur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Katharine J. Dell, "Studies of the Didactical Books of the Hebrew Bible", in Magne Sæbø, Peter Machinist and Jean Louis Ska,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a Century of Modernism and Historicis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3), 603-624. [45] Addison G. Wright, "Additional Numerical Patterns in Qoheleth",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45 (1968), 32-43; Addison G. 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of Qoheleth",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30 (1968), 313-334; Addison G. Wright,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Revisited: Numerical Patterns in the Book of Qoheleth",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42 (1980), 30-51. [46] 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47] Daniel Weidner, "Secularization, Scripture, and the Theory of Reading: J. G. Herder and the Old Testament", Secularization and Disenchantment 94 (2005), 169-193. [48] Ryn, A Common Human Ground: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pp. 69-70. [49] Margaret Scotford Archer, Making Our Way Through the World: Human Reflexivity and Social Mo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4-29; Ryn, A Common Human Ground: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50] 如刘家和,“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51] 参见蔡锦昌,“以古贬今的政治社会思想史——李奥•史特劳斯<自然正义与历史>评述”; 杨庆中、廖娟编,《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丛书,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 |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