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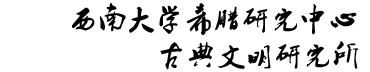
| 张绪山:论经院哲学对近代科学思维的贡献 |
| (发布日期: 2016-05-10 10:09:57 阅读:次) |
论经院哲学对近代科学思维的贡献*
张绪山
摘要:经院哲学是神学和逻辑的结合物,其特点是利用逻辑手段论证神学教条和教义,以增强其说服力。它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逻辑分析传统,在服务神学目的的前提下,将逻辑的思辨功能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使已经确定的信仰对象变成了思辨的对象,促成了怀疑精神的产生。经院哲学对近代科学的贡献在于:一、确立了对上帝理性的坚定信仰,即相信上帝为自然和宇宙设定秩序,每一事物都受到上帝的监督并被置于上帝的秩序之中。近代科学产生的前提,即对自然界和谐秩序的信仰由此产生。二、经院哲学培育的严格的逻辑论证传统,在经院哲学所服务的信仰目标被否定以后流传了下来;这种逻辑传统进一步发展,上升到数理逻辑阶段,演变成近代科学思维。三、经院哲学孕育了近代科学思维的实验观念。古代希腊的重要逻辑遗产走向近代的科学思维,经受了经院哲学的改造和加工这个中间环节;无视经院哲学在古代文化遗产和近代科学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作用,不符合历史事实。 关键词:经院哲学 近代科学思维
近代科学在西方的勃兴,历来被视为欧洲的“奇迹”之一。对于这一“奇迹”产生的原因,研究者或以欧洲社会的巨变来说明,或以欧洲的智力优越性来解释,皆难得正鹄。就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而言,经院哲学与近代科学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不可脱离之内在联系;欧洲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内在精神的形成,实得益于经院哲学的积极贡献。经院哲学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不应被完全视为历史长河中的负面遗产。
一、近代科学思维由经院哲学脱胎而来 近代科学的根本要素有两个:一是科学各学科取得的具体成果,一是统御各学科的思维方式,即理解和认识自然世界的法则。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形成于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中叶。在这两个多世纪中,欧洲近代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确立了与之互为里表的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对应的事件是文艺复兴运动,因此可以说,近代科学思维方式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后期的产物。 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成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强大力量,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对于促成这种大变化的原因,却历来人言言殊,难得要领。有人坦然承认,“把促成这种变化的一切因素与见解聚拢在一起,观察者仍然觉得在这一切背后还有一种生气活泼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只能很不完全地捕捉到。它有力量把其余的因素掺和在一起,使其突然成为一个整体。这种现代精神以可惊的速度形成,我们还不能充分解释其过程。”[1]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社会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变化上解释科学的巨大发展。恩格斯认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2]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角度,这样的解释自然是正确的。这是就人类精神活动的根本物质基础而言。不过,人类每一种精神活动,都是以它从以往历史中继承的人类文化精神遗产为前提。科学思维作为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以它所继承的前一个时期的精神遗产作为出发点。那么,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精神文化前提是什么? 科学史家丹皮尔(1868-1952)说:“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我们这个世纪。”[3]就科学发展进程而论,文艺复兴时期与丹皮尔所说的“我们这个世纪”即20世纪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尽管这两个时期的各自特点不尽相同。希腊的极盛期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则不然。如果罗马帝国可勉强视作希腊文化的继承者,那么,从罗马帝国衰亡到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中世纪”,在文化形态与希腊罗马文化迥然不同。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精神统治,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古代希腊极盛时期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特别是公元500年到1000年之间的五个世纪,更是西欧文化发展的低谷,故又被称作“黑暗时代”。这种状况是罗马帝国自3世纪危机以后古典文化衰落之势的延伸,同时也是蛮族(日耳曼人、维金人、匈牙利人等)入侵造成的必然结果。 罗马帝国承载的古典文化的式微,蛮族入侵对罗马帝国文化断壁残垣的扫荡,造成欧洲尤其是西欧文化的空白状态,为混乱状态中稍有能力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督教组织确立其精神独尊地位提供了条件。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中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缺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教士们——引者注)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4]作为中世纪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经院哲学是近代科学兴起前的主导意识形态。近代科学的兴起和经院哲学日渐衰落是前后相继的两个文化运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消此长、新陈代谢的关系。近代以来科学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显然并非直接继承古希腊的文化遗产,而是脱胎于经院哲学这一精神遗产。因此,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离开它的经院哲学遗产,是不可思议的,在逻辑关系上是难以理解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经院哲学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是什么?这种联系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二、 经院哲学的本质特点:神学与逻辑的结合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Scholasticus,意为“经院里的学问”。一般认为,8-10世纪是经院哲学的酝酿期,11-13世纪是其兴盛期,14世纪以后它在欧洲思想舞台上已逐渐衰微。经院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经院哲学指修道院中的职业神职人员从事的神学研究;不过,12世纪以后大学日渐成为欧洲大陆文化活动的中心,经院学术的中心也大部转移到大学,所以,广义的经院哲学是指11-13世纪的学术活动,既包括基督教神学院中的神学研究,也包括中世纪大学内部的学术研究,也就是说,它指的是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习惯方式。 经院哲学是此一阶段神学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其本质仍然是神学,但它依赖的工具是“辩证法”和三段论的推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主要是逻辑学)引进神学体系,将神学和哲学加以调和,形成一种思辨体系;它以一个既定的神学命题为前提展开思辨论证。由于经院哲学家在思辨论证时抛开一切现实性的经验,在神学的抽象概念中绕圈子,所以在气质上表现为“繁琐的与好辩的”特征。[5]在经院哲学的论辩中,理性的逻辑被限定在神学世界中,与客观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人类实践活动没有关联。因此,恩格斯称它是“一种象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6] 经院哲学内部有三种思想倾向;一是将理性当作神学信条的裁判者;二是在神学研究领域根本拒斥理性;三是使神学和理性调和,但使理性服从神学。在经院哲学发展里程中,第三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把基督教会的教义建筑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其次,对教会的全部教义加以系统的研究。[7] 经院哲学的一切矛盾由此而生发出来:神学教义是前提,它不允许理性思维超出神学既定教义的大范围;但它又借助理性思辨来论证其教条和教义,驱使哲学为神学服务,其结果是理性的逻辑论辩在神学这个崇高的对象面前充当了“奴婢”的角色。但是,神学要利用哲学这个奴婢,在客观上不能摆脱哲学的理性思辨功能,于是,不仅不能扼杀,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它;在经院哲学的神学范畴中,哲学固有的理性思辨功能不仅得到保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培育与发展。经院哲学家追求神学的说服力量,追求逻辑论证的完美,在客观上推动了理性与逻辑的发展。这一特点几乎见于所有的经院哲学家的智力活动。 安瑟伦(1033-1109)是11世纪经院哲学实在论的最大代表。他是将逻辑三段论娴熟地运用于上帝存在论证明的代表人物。在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上,虽然他强调“基督教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但他同时又指出,“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信仰”,“当我们有了坚定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8]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是基督教教义的权威解说者,虽然他坚持“神学高于哲学,哲学乃神学奴仆”的原则,认为“神学可能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它不可。”但他又坚持认为,基督教的某些基本真理可以不用启示的帮助,而单靠独立无助的理性得到证明。[9]因此,他承认在人的一切欲望中,智慧的欲望是最令人欣慰的;[10]在阿奎那的神学著作中,有一种对哲学事业的尊敬和一种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运用它的决心。在阿奎那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中,唯理主义和基督教化的神秘主义,希腊人的知识和教会的说教,天启和理性结合起来了。哲学的思辨论证提高了神学的灵活性,其自身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经院哲学把哲学作为捍卫神学信仰的工具,维持了理性的地位和权能。 神学将理性与思辨作为一种工具加以利用,使已经确定了的信仰内容变成了思辨的对象。这在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论争中尤为明显。唯名论者贝伦伽里(约1000-1088)反对共相(即抽象概念)是真正的本质,认为“实体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他讨论重要宗教信条圣餐化体(Eucharist)说,认为圣餐仪式中人们所“吃”的是普通的面包,“喝”的是普通的酒,而不是教会所称的“主的肉和血”;圣餐礼只具有精神的象征意义,因为基督的身躯已“升至天国”,怎么能在圣餐礼中“临在”呢?人们怎能吃、喝天国里的东西呢?即使主的身躯大得如耸立的巨塔,被如此多的信徒吃喝,岂不早被吃得一干二净?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中,诸如此类的辩驳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尤其是,神学教条并没有也不可能回答理性思维提出的所有问题,为理性思辨留下极大的空间。如基督教教义中末日审判时死者复活受审的问题,经院哲学家往往进一步讨论:人的肉体是否复活?死后的人在什么年龄复活?复活时是作为儿童还是青年?外貌如何?是瘦子还是胖子?等等。经院哲学将这些问题纳入逻辑论辩的范围并展开激烈论证,其方式是繁琐的,但作为一种思维训练,对于思维方式的形成无疑大有助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刻意的挑剔性的诘问和辩难,是逻辑思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科学思维方式中的逻辑严格性在这里得到孕育。 理性思维的存在促成了怀疑精神的产生,尽管在中世纪的精神氛围中,这种怀疑不可能达到否定教会信条的地步。12世纪法国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彼埃尔·阿伯拉尔(1079-1142)针对“信仰而后理解”,大胆提出“理解才能信仰”。虽然他并不怀疑《圣经》的权威,并公开声明“我不想成为一个与保罗发生冲突的哲学家,也不想成为与基督脱离关系的亚里士多德”,[11]但他对教会所依赖的教父们的著作却表示出强烈的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人的著作中有不少矛盾或难解之处,对“所有这一类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没有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否则一切研究的道路都要被阻塞。”他坚持“怀疑是研究的道路”,“研究才能达到真理”。他在《是与否》中写下的一段文字,集中体现了经院哲学家所具有的一种充满活力的信念: “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的和经常的怀疑。在所有哲学家最有眼光的亚里士多德,首先希望这种怀疑精神,因为在他的《论范畴》中对研究学问的人作过如下的劝勉:‘除非经常探讨这些事物,否则很难获致一个正确的结论。怀疑每一点都不是无益的。’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12] 阿伯拉尔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经院教师之一,有众多学生追随他求学问道。他在教学活动中所依靠的是他的雄辩而犀利的思想力量,而不是依靠传统。[13]在西方神学家中,他首先建设性地运用怀疑精神和批判方法,研究神学体系中各方面的问题。他的体系中的独到见解,对当时或后来,都没有引起多大反应,但是他的方法却为他的后继者所普遍采用。[14]阿伯拉尔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对教会权威的抵抗……对盲目的信仰进行永不松懈的斗争。”[15] 阿伯拉尔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孤单,当时新兴起的大学所代表的智力复兴势力有一种共识性的要求,即在神学范围内“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证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宣布福音。他们曾这样说:无法理解的言辞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16]在当时的传统中,这种见解是一股具有强大潜力的新兴思想潮流。随着翻译运动的深入,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运用在13世纪以后则呈现出系统化的趋势。大阿尔伯特(1206-1280)明确提出“逻辑是科学方法”,在《论逻辑的性质》一文中写道:“这门科学(逻辑)是一切哲学的方法,它不是哲学的一部分。” 经院哲学充分运用哲学的思辨功能,在表面上达到了维护信仰的目的,但造成的后果是,它在不间断地运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过程中,发展了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古希腊逻辑分析传统,对思维的发展“不失为某种精确性的一个训练。”[17] 而且,经院哲学企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单一的逻辑体系,不可避免地对几乎所有事物提出明确的见解,这使它很容易卷入对所有问题的论战。在论战中又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理性与逻辑。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经院哲学确立了信仰对于理性思辨的依赖关系,思维方式中的理性逻辑原则也由此得以确立。费尔巴哈说:“经院哲学是为教会服务的。因为它承认、论证与捍卫教会的原则。尽管如此,它却从科学的兴趣出发,鼓励和赞许自由的研究精神。它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它力图证明和论证仅仅立足权威之上的信仰的对象,从而证明了——虽然大部分违背它自己的理解和意志——理性的权威,给世界引入一种与旧教会的原则不同的原则——独立思考的精神的原则,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或者至少是为这一原则作了准备。”[18]这个分析是准确的。 思维的逻辑原则是经院哲学对于欧洲文化最有价值的贡献,它提高了人类理性和理性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2世纪欧坦的贺诺琉斯(Honorius von Autun)说:“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不存在别的权威;权威教导我们信仰的东西,理性以它的证据替我们证实。逻辑推理的理性,证明圣经有目共睹的权威所宣布的东西:即便是全体天使都留在天堂,人连同他的所有后裔也会被创造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的,而我所理解的世界是天、地和宇宙包含的一切。要是相信如果众天使继续留在天空,人类就不会被创造出来,那是荒唐愚蠢的,正像我们读到的,正是为了人宇宙才被创造出来。”[19]人和人的理性在上帝这个前提下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经院哲学在借用希腊知识遗产的过程中,采用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古典宇宙观念,将他视为最高权威,将有关宇宙即上帝、人和自然界的全部知识,包括可以从观察和理性获得的,以及来自启示、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知识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连贯的理性体系,并认为它们是基督教神学的定论,因此,教会在维护它的权威性时,便不得不与文艺复兴以来反抗亚里士多德宇宙观念的近代科学发生冲突,并利用它的巨大力量迫害近代科学家。这是经院哲学留给近代科学思维的双重遗产。
三、 近代科学思维对经院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欧洲近代科学思维方式”,指的是在欧洲近代社会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的思维习惯,以怀特海的说法,是指这一时期“有素养的思想家中一种盛极一时的传统习惯。”[20]。爱因斯坦(1879-1955)认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21]因此,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思想可以视为近代科学思维的主要特征。 近代科学思维的这两大特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共识。如有的科学史家说:“实验法可以认为是科学的一条腿,而另一条腿是希腊-巴比伦的逻辑的数学遗产。”[22]又有科学史学者指出:“(1)刻卜勒、伽利略、牛顿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方法意味着把知识限制于现象世界以及这世界的量的方面。(2)它以细致的观察补充理论分析,并通过精密测量来检验论证。”[23]我国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说:“科学的具体形式及实质部分,是各部门的知识,但科学包括获得这些知识的全部程序,如现象的观察和度量,由此形成或建立若干概念(基本的,及由此界定的观念),观察及度量结果的归纳和伸引,建立观念的函数关系(成为定律);新观念的创立,实验的构想和计划,数学方法的采用和创造;以想象力创造理论(假设物理观念间的新函数关系),根据逻辑方法作演绎,推出新的函数关系,以实验测证这些关系以及其所由出之理论。”[24]对于现代科学家而言,逻辑(归纳、演绎)原则和实验原则已经是科学思维的不证自明的两个基本要素,犹如飞鸟必有两翼一样自然而然。 近代科学思维产生的一个前提因素,是相信自然界存在理性可以认识的秩序。正如怀特海所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近)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25]这种信念是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中逻辑原则和实验原则之上的统御原则。在欧洲科学思想史上,自然秩序观念最初表现在古希腊悲剧思想中的不可改变的命运必然性和维护城邦生活的城邦法中,罗马时代表现在罗马法的秩序观念上,而在经院哲学中则是对上帝理性的坚定信仰,即相信上帝为自然和宇宙设定秩序、每一事物都受到上帝的监督并被置于上帝的秩序之中。以12世纪法国的沙特尔修道院中发展起来的沙特尔学派为例。这个学派并不否认上帝创造世界的创世说,但它认为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合理的整体。康歇的威廉(William von Couches)和阿尔诺·德彭涅瓦尔(Arnaurd de Bonneval)认为:“上帝把属下各物按地点和名称作了区分,给众事物就像给一个巨大身躯的四肢,分配了相应的尺寸和功能。在上帝那里,甚至在始初的创造时刻,不存在任何混乱,任何混沌,因为在创造中事物就已经在它们的实体中形成了适当的类别。”[26]由于上帝赋予自然世界以秩序,自然世界成了理性可以认识的对象;认识自然要服从于认识上帝这个最终目标,认识自然变成了认识上帝的手段。 进入近代以后,“上帝为自然或宇宙设定秩序”的观念保留下来,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牢不可破的信念。牛顿说:“真理是在简单性中发现的,而不是在事物的多样性和纷乱中发现的。至于世界,它向肉眼展示出客观事物极其多种多样,在用哲学的理解去概括时,会显示出其内部组成是很简单的,以致理解得如此之好,从这些眼光来看它就是这样。正是上帝工作的完好,以最大的简单性将它们全都创造出来。”[27]1727年英国诗人亚历山大·珀薄为牛顿逝世撰写的墓志铭:“自然和自然的规律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诞生吧!于是一切都已照亮。”显然,在牛顿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科学家的使命,是寻找和发现上帝创造但被隐藏在黑暗中的自然秩序(或称规律)。爱因斯坦说:“没有可能用我们的理论结构掌握实在的信仰,没有我们世界内在和谐的信仰,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仰是并将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28]在爱因斯坦的观念中,对“世界内在和谐”即秩序的信仰一如既往。因此,我们探讨欧洲近代科学思维中的这一因素的发展历程,不能忽视经院哲学所确立的上帝的理性观念、上帝理性下的自然秩序观念这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上帝的秩序观念之下,经院哲学涉及到人类如何认识人和自然或宇宙的问题。经院哲学既以理性逻辑来认识上帝,则必然同样会以它来认识上帝的创造物,即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自然世界。13世纪阿奎那完成了理性和信仰的综合,确立了理性服从信仰的原则,但他同时也肯定了理性的作用,对二者的关系做了说明,认为神学源自信仰,而哲学源于自然理性,二者对象不同,但服务于共同的目的,即认识上帝。邓司·斯各特(1263-1308)以上帝万能为由,认为理性不能认识上帝,使理性具有摆脱信仰的倾向,为14世纪信仰和理性的分离铺平了道路。[29]他的学生威廉·奥卡姆(1300-1350)把理性和信仰分离的观点向前推进。他认为信仰和理性是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信仰只能以“天启”为基础,要合理地证明信仰是不可能的,上帝的真理只有通过信仰来领悟,而上帝真理之外的真理要由理性来认识,人类理性的运用范围限于所能看到或直接感受到的事物。这就是著名的“双重真理论”。 将理性与信仰分离开来,目的是为了防止理性损害信仰,但它有助于确立理性在认识自然和俗世事物中的作用,是理性向自由思维跨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假若理性一直为神学信仰这一主体所束缚,那么理性就永远不会投向自然研究,更不会考虑去揭示自然内部的规律。近代科学研究走上自然研究的道路,与经院哲学家所提供的上帝理性观和“双重真理论”密不可分。 理性思维脱离神学目标后首先将世俗事物作为审视的对象,这就是14世纪以后出现的世俗理性的复兴。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希腊拉丁古典文化和文物的研究,是世俗理性复兴的直接原因和动力。15世纪中叶更受到拜占庭学者的有力推动: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许多拜占庭学者携带古希腊抄本逃往意大利,向西欧人打开了古希腊灿烂的文化宝库,展现了一个与神学迥然殊异的崭新的世俗世界,在这种世界中,没有教士阶级的统治,也没有武断的信条,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人间或天上的一切事物,如世界的构成、事物的普遍结构、物质的实体、人的本性和命运等主题。在希腊古代手抄本和雕像艺术展示的新世界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30]经院哲学中发展起来的理性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形成世俗理性思潮,即人文主义;这种世俗理性思潮鼓励人们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为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而遁世冥想。[31]它明确肯定人和人的理性的重要性,告诉人们人世生活不是无足轻重的为来世的准备;人是万物之灵,人类拥有崇高的权威和尊严,人性和人生具有其他动物没有的无与伦比的价值;人之不同于禽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理性使人掌握知识,具有智慧,创造财富;理性使人高尚和完善,使人创造幸福生活,改变人生的价值。它甚至认为,理性使人具有神性,上帝的高贵只不过是具有更高超的理性。拉伯雷在《巨人传》中高呼:“请你们畅饮,请你们到知识的源泉那里去。…… 研究人类和宇宙,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莎士比士在《哈姆雷特》中慨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啊!人的理性多么高贵!人的能力无穷无尽……,人的洞察力多么宛如神明!”理性从神学设定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思维对象上的新飞跃:人类的理性思维转向了人本身。 15世纪后半叶世俗理性转向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对于近代时期进行自然研究的人来说,经院哲学中严格的逻辑造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它使“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扎根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且在找到之后坚持这种观点的可贵习惯”。即使那些对经院哲学极端厌恶的人,对于经院哲学造就的理性逻辑严格性,也在潜移默化中加以接受。伽利略“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32] 笛卡尔以反对经院哲学著称,但他得益于经院哲学的地方也很多,“如果不坚持把笛卡尔主义同经院哲学对照起来看,就无法理解笛卡尔主义。笛卡尔主义鄙视经院哲学,但本身又植根在经院哲学之中;因为笛卡尔主义采纳了经院哲学,由此人们可以认为,笛卡尔主义从经院哲学中汲取了养料。”[33] 近代自然科学研究将世俗理性向前更进一步,达到了逻辑的数学表达阶段。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思维的重要成就之一。[34]这种思维习惯是这一时期思想人物的重要特征。达·芬奇强调:“那些真正的科学满怀希望,通过五官深入钻研,使争论者哑口无言;它们并不拿梦想来哺育研究者,始终根据那些真实不虚的、人所共知的根本原理一步一步前进,循着正确的次序,最后达到目的。这一点在普通数学里是很明显的,研究数的代数和研究量的几何就把不连续量和连续量讲得十分正确。”他又说:“人类的任何探讨,如果不是通过数学的证明进行的,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35]伽利略说:“哲学是写在那本一向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巨大的书即宇宙之中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会用来写它的语言,弄懂其符号,那我们是无法理解它的。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和其它几何图形,而没有这些符号的帮助,那是连一个字也不可能理解的。没有它们,我们只能在黑暗的曲径中彷徨而一无所得。”刻卜勒则更进一步,在他看来,数学不单纯是一个可以有益地用于研究过程的工具,而且是唯一使科学分析成为可能的前提,事物的量的特征是唯一能理解的方面。除了量或借助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到。[36]在牛顿那里,数学表达成为科学思维的重要原则。他认为科学是自然界过程的精密的数学表达。他说:“我希望指出(像应有的那样有例子予以说明),数学在自然哲学中是多么宝贵,因此献身于自然哲学的人就要首先学习数学……依靠哲学方面的几何学家们和几何方面的哲学家们的帮助,真正地取代了到处宣扬的猜测和可能性,我们就将最终地建立有最主要的证据所支持的自然科学。”[37] 近代科学思维的数学逻辑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直接回到古希腊逻辑体系,但它的实际起点却是经院哲学的理性与逻辑思维。所以有学者指出,“在被人们错误地称为‘蒙昧主义的’中世纪里(我要重复这一点),神学,一种典型的理性化之举诞生了。什么是神学?当然,它承认启示的真理,但它随即转向那些不太理解启示的人,异端分子、无神论者,以便向他们证明这一神圣真理的真理性。其实,神学在于凭借自然认识的方法(根据神学家们的用语),即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的这种理性的方法,去证明超自然的认识。这种理性恰恰与当时的理性相同。新颖之处(是)……哥白尼-伽利略之举,特别是伽利略之举,不再使用日常语言去构思这种理性,而是选取数学语言作为范例。”[38]可以说,从经院哲学理性到近代科学数理逻辑,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近代科学家反对乃至激烈抨击经院哲学把理性与逻辑严格限制在神学范畴的做法,造成了近代科学与经院哲学在形式上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使后人忽视了其内在联系性的存在。 实验观念作为近代科学思维的另一特点,也经历了经院哲学的培育。理性和信仰严格分离的思想,在中世纪晚期思想领域表现为两个重要特征,即理性思维的独立和不涉及逻辑推理的虔诚神秘主义的发展。理性脱离神学后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自由地与实验研究结合。虔诚神秘主义则使许多思想家以极端的形式重新复活奥古斯丁的先定论,以上帝的权威否定教会的权威;同时,对直接感官知觉对象的重视,打破了人们对抽象观念的信仰,促进了直接的观察与实验,促进了归纳研究,包括炼金术的发展。[39] 实验观念进入经院哲学家的意识中。早在13世纪,英国林肯郡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1175-1253)就已“感到需要从实验得出一般原则,需要利用数学的演绎推理然后根据事实来检验这种推理。”[40]经院哲学内部激进的唯名论思想家罗吉尔·培根(1214-1294)受格罗塞特的影响,认为认识有三种方法,即权威、实验和判断;如果不以理智为前提,那么权威不能给我们以确定的知识;如果不以实验来检验,那么判断从自身中不能在证明中区别诡辩论,因此只有实验科学才是认识的真正道路。[41]他指出:“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因为获得认识有两种方法,即通过推理和通过实验。推理做出一个结论,并使我们承认这个结论,但并没有使这个结论确实可靠。它也没有消除怀疑,使心灵可以安于对真理的直观,除非心灵通过经验的方法发现了它;……所以只有推理是不够的,还要有经验才充分。”[42] 他主张,真正的学者应靠“实验来弄懂自然科学、医药、炼金术和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他曾研究过平凸镜的放大效果,并建议制造望远镜。[43]罗吉尔·培根思想中的“实验”是指以特定目的为指向、以特定手段进行的科学实验。他一生在物理、化学和光学等方面做过许多实验,是公认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 实验主义认识论在14世纪时形成一股思潮。14世纪的炼金术士费拉拉的布努斯说:“如果你希望知道胡椒是热性的,醋是冷性的,药西瓜和苦艾呈苦性,蜂蜜是甜的,草乌含有毒素,磁能吸铁,砷能使黄铜变白,而锌土(氧化锌)则能使它变成橘色,对这些事例中的任何一个,你必须通过经验来确证其可信性。在具有某种实用目的的实用性范围的地理学、天文学、音乐、透镜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学科领域里,情况也是这样。……和其他所有类型的现实的自然观一样,这种对真理和公正的探索必须用实在的实验来加以验证。除此而外,无论如何是实现不了这种探求的。”[44]达·芬奇更明确地指出:“在我看来,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那些不是从经验里产生、也不受经验检定的学问,那些无论在开头、中间或末尾都不通过任何感官的学问,是虚妄无实的、充满错误的。”[45]他告诉人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一个科学问题时,我首先安排几种实验,因为我的目的是根据经验来解决问题,然后指出为什么物体在什么原因下会有这样的效应。这是一切从事研究自然界现象所必须遵循的方法……我们必须在各种情况和环境下向经验请教,直到我们能从这许多事例中引伸出它们所包含的普遍规律。”[46]伽利略也有同样的说法:“我认为在讨论自然问题时,我们不应当从《圣经》段落的权威出发,而应当从感觉的经验和必然的证明出发。”[47]在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中,实验观念被提高到了与数理逻辑同等乃至更为重要的地位。 近代科学思维异乎以往思维方式的显著特色,是重视和坚持实验原则与逻辑原则的密切结合,认为真理必须经历这两种手段的检验。达·芬奇说,“人类的任何探索,如果不是通过数学的证明进行,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如果你说那些从头到尾都在理性中的科学才有真理性,那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有很多理由否定这个说法,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这种理性探讨里毫无经验,离开了经验是谈不到什么可靠性的。”[48]伽利略是公认的近代科学实验之父,但他并非只是以实验进行研究,爱因斯坦指出:“任何一种实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而且任何一种思辨思维,它的概念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经验材料。把经验的态度同演绎的态度截然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而且也不代表伽利略思想。……伽利略只是在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及其门徒的前提是任意的,或者是占不住脚的时候,才反对他们的演绎法;他强调说,……即使是最讲得通的演绎,如果同经验的判断不符,也应当被抛弃。另一方面,伽利略自己也使用了不少的逻辑演绎。”[49]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认为,科学研究上的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只知道收集,而理性主义者则好像蜘蛛,只知道织网。真正的科学研究应采取蜜蜂的方法,从花园和田野里采集材料,然后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50]培根将他的实验方法确定为“学术经验的设计”,总结了八种实验方法。“实验和理性”的密切结合,尤其是实验原则被置于突出位置,是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逻辑原则和实验原则二者的密切结合已经达到自觉阶段,这是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已经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 经院哲学在欧洲科学思维发展史中的地位 对经院哲学的批评始自文艺复兴时代。当时的人们认为自己所处时代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重新复兴的时代,是与基督教会一统天下的中世纪对立的。在他们强烈否定中世纪文化的激情中,自然不会对经院哲学给予客观的认识和评价,经院哲学的神学形象也不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好印象,所以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对它表现出本能的厌恶和情感上的对立,认为由经院哲学而来的教育方式无益且愚蠢。在这种情感倾向中,经院哲学作为一个过时的事物,变成了一个可笑且可恶的对象。 彼得·拉谟斯(Peter Ramus, 1515-157)对经院哲学教育方式的态度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花了3年6个月的时间研读经院哲学。之后,根据大学规定,研读了《工具论》里的各篇论文,进行讨论,再做一番苦思冥索(在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中,那些论述论辩的著作在3年课程里,尤其要一读再读)。按部就班地做完那一切以后,我合计了一下埋头于经院学问的日子。很自然地,我开始寻找运用那些废寝忘食而习得的知识的目的。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那些篇章既没有给我以更多的历史和古代知识,没有使我的辩才有所长进,也不能使我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不能使我更机敏更圆滑一些。呵,多么地无知,多么地让人忧伤!在经历过潜心万苦之后,我却采集不到、哪怕是看一眼那些被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辩里能找到的异常丰富的智慧之果!我该怎样悲叹我不幸的命运、贫乏的思想!”[51]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直接承受了经院哲学的传统遗产,最能体会到将思维对象局限于狭隘的神学内容对活跃的思维造成的严重束缚。 近代以来哲学家评论经院哲学时,基本上沿着同样的思路,抨击其思维内容的脱离实际和狭隘空洞。黑格尔认为,经院哲学整个讲来“完全是野蛮的抽象理智的哲学,没有真实的材料和内容。……它只是形式、空疏的理智,老是在理智的规定、范畴的无有根据的联系中转来转去”;“完全是抽象理智的紊乱,象北日耳曼自然景象中多枝的枯树一样。”[52] 列宁指出:“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寻求、探索,它接近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的逻辑学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53] 很显然,逻辑思辨活动在思维材料上的有限性和不自由,造成了思维成果的贫乏,这是近代以来经院哲学遭受诟病和攻击的最大弊端。 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的前苏联学者强调经院哲学的阶级属性,认为“经院哲学最初的‘繁荣’一方面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哲学界得到极其广泛的运用有关。经院哲学体系具有妥协性,为了正统思想的需要,力图利用新思想的萌芽和新的材料。另一方面,所谓‘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是极反动的正统天主教思想体系的表现和巩固。中世纪的黑暗势力终于在这个体系中形成。在这个体系中,‘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被巧妙地与论鬼神的学说相结合,与对女巫和异教徒的辨识和扑灭之指导结合,并用于论证罗马教会的世界统治。维护劳苦群众所遭受的那种残酷的剥削,为封建的等级制度辩护,窒杀进步的思想,——这就是经院哲学体系的真实意义和目的。”[54]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明显地折射出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子。 但是,从科学思想史演变的角度,此类认识都没有从人类思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角度考虑两种思想形态的关系,同时还忽略了一点:经院哲学是中世纪的黑暗状态的“后果”,而非原因;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对经院哲学的地位的认识和评价,必须将它置于整个欧洲科学思想的演变过程中。 我们知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在古希腊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希腊人依靠“天才的直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说法)创造了至今仍令人赞叹的科学成就。但古希腊的衰落和罗马帝国的征服,结束了希腊文化的繁荣局面。罗马人的兴趣和贡献在军事活动和国家管理方面。4世纪基督教被确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标志着古希腊文化精神已在制度上退出历史舞台。390年,罗马皇帝下令禁止异教活动,415年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女数学家希帕提亚被基督教徒杀害,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封闭柏拉图创建的活动近千年的雅典学院,这一切说明欧洲进入信仰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日耳曼各族的入侵在欧洲尤其是西欧造成的动荡,在几个世纪中维持了欧洲文化的荒芜状态。8世纪末9世纪初,加洛林帝国形成,查里曼利用当时的文化条件,举办教会学校和宫廷学校,鼓励和推动教士们学习,以上帝最喜欢的“最谦虚的态度,热烈钻研,以求更容易地、更正确地探索《圣经》的奥秘”,一时间出现了“加洛林文艺复兴”。这一运动的贡献,主要在于发现和保存了一些古典文本。但9-10世纪维金人、马扎尔人的入侵使西欧的动荡局面延续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拉丁世界所遭受的蛮族入侵风暴与5世纪的蛮族入侵一样,对文化的培植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欧洲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是从11世纪开始,入侵活动的停止,农业的进步,尤其是城市的复兴和人口的增长,使欧洲社会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和理智复兴时期。11世纪以后经院哲学的兴盛,是理性活动逐渐复苏的标志,是整个西欧社会物质和精神变化的具体体现。在这种理智复兴中,有两大文化运动与经院哲学联系在一起,其一是是翻译运动的发展;其二是大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运动的发展和大学的兴起是互相关联的事物,但对经院哲学的发展而言,二者的作用有所区别:翻译运动为经院哲学提供了新的思维资料并影响到它的思维方式;而大学的兴起则为经院哲学提供了一个舞台,对其存在和连续性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 拉丁世界对古典文化的吸收在12世纪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被人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种说法是否合适,曾有过讨论,[55]此处不加涉及。但古典文化重新抬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时期为人熟悉的古代人物有维吉尔、奥维德、卢坎、贺拉斯、西塞罗和塞内加;同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通过评注者的著作得到研究和重视;法学领域则是《查士丁尼法典》的重新发现。法国沙特尔地方的伯纳德说过一句名言:“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说明当时的人们认识到古典文化遗产的巨大恩泽。[56]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叶,拉丁世界通过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吸收古典文化的养料。这一运动的材料来源有两个:一是阿拉伯典籍,二是拜占庭帝国的典籍。这两方面提供的古希腊典籍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注入拉丁世界。7世纪中叶崛起的阿拉伯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基本上控制了地中海水域,全面接触到希腊罗马世界的文明成果,在惊讶之余开始了积极吸收过程,在1000年之前的三个多世纪中几乎将全部希腊医学、自然哲学以及数学著作译成了阿拉伯文。11世纪,随着拉丁世界从穆斯林手中重新夺回西班牙(特别是1085年夺回西班牙重镇托莱多)和西西里岛,阿拉伯古籍保存的古希腊文化科技成果通过翻译运动又回流到拉丁世界。12-13世纪从事翻译的众多名家中,以意大利克里莫纳的杰拉德(约1114-1187)最为杰出,他一人翻译的著作达70-80部,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盖伦、托勒密、花拉子模、阿维森纳等人的论著。拉丁世界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从未完全中断,12世纪从希腊文翻译希腊典籍的事业重新开始,威尼斯翻译家因与拜占庭学者保持联系,翻译了一批亚里士多德著作,12世纪中叶托勒密和欧几里得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13世纪穆尔贝克的威廉(活跃于1260-1286)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文集和集注,与许多新柏拉图主义作家的著作及阿基米德的数学著作。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和注释,促进了西欧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正是这些古希腊著作对经院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7] 这种影响通过中世纪的大学这种教育机制发挥出来。中世纪大学的前身是城市学校。城市学校随城市兴起而产生,其中最出色的是那些教堂学校和教区教士经营的各种公立学校。这些学校并不直接服务于培养教士这一目标,而是面向任何可以负担费用的人。这一时期法国各城市如巴黎、奥尔良和沙特尔各学校以严肃的数学研究著名;意大利波洛尼亚等城的学校以法学教育名闻遐迩;英国的牛津各学校在法律、神学和人文艺术方面享有盛誉。城市学校在复兴世俗理性方面的努力为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兴起的大学所继承,其哲学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课程体系中,包括《圣经》和神学研究上。大学兴起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受教育者人数的增加。以最早的几所大学论,14世纪波洛尼亚大学的学生数量可能在1000-1500人,牛津大学的规模大致相同,巴黎大学的学生数量最多时达2500-2700人。但是,如果不是伴随着教育内容的改变,则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必然大打折扣。翻译运动提供的大量新的思想资料迅速进入大学教育内容。传统“七艺”各科的比重已发生变化,其中文法的重要性下降,逻辑学的作用上升;伦理哲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进入大学课程;医学、法学和神学是最高级的课程。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自然哲学教育中,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成为核心内容,13世纪下半叶,他的形而上学、宇宙论、物理、天象学、心理学和自然史著作成为大学的必修课程。新的思想材料注入大学,犹如清澈的溪流注入干涸的土地,使拉丁欧洲几近枯萎的思想田园迅速恢复生机。新思想材料成为新理智运动的刺激源,欧洲各地的学子聚拢到牛津、巴黎或波洛尼亚等等的学术中心以后,参与热烈的辩论活动。重新活跃的学术活动使学生们的心智处于一种昂扬激荡的气氛中。[58] 大学教育内容的变化影响到经院哲学,主要是因为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差不多同时都是经院神学家。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进入大学,必然影响到经院哲学,其后果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和自然哲学被教会纳入神学体系,取得了神学教条的地位。从本质上,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开放性的,它允许质疑和讨论,于是,作为教条的亚里士多德宇宙论和自然哲学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成为大学内部的学者——同时也是神学家——争议的对象,集教授和神学家于一身的学者们由此而分化开来。这一特点可以解释亚里士多德哲学,尤其是他的宇宙论和自然哲学何以在教会的权威下,成为以天文学革命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严重障碍,造成不利影响;也可以说明,对科学思维方式做出贡献的中世纪学者,为何几乎都是大学中任教的神学家,如格罗塞斯特是牛津大学的学者和该大学第一任校长;罗杰尔·培根曾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并在巴黎大学任教;大阿尔伯特曾在帕多瓦大学学习,在巴黎大学任教,并在1248年受命创立科隆大学;托马斯·阿奎那曾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在巴黎大学任教,邓斯·司各特曾在牛津学习,在巴黎大学任教,威廉·奥卡姆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有学者对大学制度进行细致的考察后承认:“描述中世纪的陈词滥调把教授刻划得毫无骨气、充满奴性,把他们描绘成亚里士多德和神父们的卑屈追随者……丝毫不敢偏离权威的指挥。当然,的确是有很多神学上的限制,但是在这些限制的范围内,中世纪学者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几乎没有一项教条,不论是哲学的还是神学的,不曾受到中世纪大学学者们细致的审查和批判。可以肯定地说,中世纪的学者,特别是那些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古代或宗教权威的限制和压迫。”[59]的确,只要学者们研究成果不对神学信条造成致命威胁,教会就不会走向极端。 考察经院哲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不能忽视一个明显的事实:对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近代科学家本身,差不多都具有大学教授和神学家双重身份,无人不具有神学信仰。如哥白尼(1473-1543)曾在克拉科夫大学和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和帕多瓦等大学学习,但他又担任教士职务;布鲁诺(1548-1600)则始终是教士身份;伽利略曾任教比萨大学和帕多瓦大学的教授,但他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牛顿是近代科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活动具有典型意义。他说:“上帝是一个代名词,……一个人要证明有一个完美的存在(being),却未同时证明他就是造物主或万物的创造者,则就尚未证明上帝的存在。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全智的、最完美的却无支配权的存在,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上帝的神性最好不由抽象的概念,而由现象,由它的最终原因来证明。”[60]牛顿并没有抛弃对上帝的信仰。与牛顿相类似的是,波义耳临死时留下50英镑作为讲座基金,以求论证上帝存在。在这些自然科学家那里,上帝并非不存在,上帝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关系,但自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研究对象,一个不同于上帝本身的理性可以认识的对象;在近代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家已经不再使上帝及其相关教义纠缠和限制自然研究过程,研究活动不再以上帝为既定对象,换言之,上帝被放在了一边。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坏。”[61] 如何解释基督教会对近代科学家的迫害?这要从基督教会教义学的发展史说起。“地心说”最初是由古希腊学者提出的,后经亚里士多德,特别是托勒密的阐发,形成为一种完整的学说。这一学说因符合教会主张的上帝“创世说”,而被纳入到基督教信仰之内,成为其最基本的教条之一。教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便不得不极力维护信仰体系。然而,哥白尼“日心说”所标志的近代科学革命,首先且直接冲击的正是基督教会坚守的“地心说”信条。罗素说:“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抱着真纯无暇的正统信仰……他的正统信仰很真诚,他反对认为他的学说与《圣经》相抵触的看法。”[62]事实确实如此。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导言》写道:“如果真有一种科学能够使人心灵高贵,脱离时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果真见到天主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时,必然会感到一种动力促使人趋向于规范的生活,去实行各种道德,可以从万物中看出来造物主确实是真美善之源。”不幸的是,这位怀有探寻上帝的创造物之“庄严秩序”使命的虔诚教士,其智力活动的成果即“日心说”,却颠覆了基督教教会极力维护的根本教条之一,损害了教会的权威,这如何不引起教会组织的恐慌与震怒?于是,教会组织为了维护其本身把持的教义解说权的权威,对任何忤逆的学说实施干预与惩罚,成为必然。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督教会迫害近代科学家的真相。这种情形很类似斯大林位维护自身权威以“反马克思主义”罪名对那些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所实施的迫害。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说,传教士告诉孩子们上帝存在,而牛顿则向人们证明了宇宙是上帝智慧的杰作。近代以来科学家普遍持有的信念是,上帝以理性创作宇宙,为它制定了秩序和规则,而被上帝创造并被赋予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人类的使命,则是探索被上帝隐藏的自然法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以来科学家普遍怀有宗教情怀,甚至连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能脱离这种情愫,认为“科学撇离宗教便是跛子,宗教撇开科学便成了瞎子。”可以说,即使到今天,经院哲学中培育的对上帝理性的坚定信仰,仍然是很多西方科学家探索宇宙规律的重要动力。 我们认为,对于经院哲学的评价,从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应仅仅注意它的神学性质,更应该注意它内部的活跃因素,即理性与逻辑思辨方法的积极意义。经院哲学在本质上是神学,但是,它在既定的神学前提下并不排斥理性与逻辑,相反,它极力运用理性与逻辑思辨来维护神学。经院哲学的特点是,“漠视事实和科学,在仅凭观察才能决定的事物上偏信推理,以及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区别和其精微意义。”[63]换言之,经院哲学家把锐利而深沉的智慧和大量的闲暇时间,荒废在非常有限的任何自然事例所不能证明的那些东西上,从而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繁琐论证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不过,经院哲学致力于理性逻辑的开发和运用,是不可否认的。在这种不断的机智努力中,科学思维所需要的严密逻辑推理的习惯不知不觉地培养起来了。近代科学家接受了这种必要的严格训练,转向自然现象的研究时,便形成了近代科学思维方法。从这个意义上,经院哲学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功不可没。 科学史家丹皮尔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可为不易之论:“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采取了解释者的态度;创造性的实验研究是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合的。可是他们的理性的唯知主义,不但保存了而且还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他们关于神和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收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予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再用实践去加以检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摧毁。”[64]丹皮尔所说的“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是指思维过程的神学权威前提。理性的逻辑分析原则脱离神学戒条和神学权威前提而转向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并与系统的实验相结合,是一个渐变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化遗产经受经院哲学的改造和加工后,最终走向了近代的科学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无视经院哲学在古代文化遗产和近代科学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欧洲科学思维发展史,不应该忽视经院哲学的作用,而应该对它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考察,并做出公允的评价。
On the Scholastic Origin of the Thinking Ways of Modern Science in Europe
Scholasticism, a combination of theology and rational logic,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unique way to defend its theological doctrines by rational logic. Its frequent resorts to the Aristotelian logic helped to revive the great Greek tradition of logic, and fostered the taste and habit for precision and exactnes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thinking ways of the modern science; its full use of rational logic was instrumental to sceptical[TG1] attitude to dogmatic views, and thus bring logical rationalism into the theology which is to a large extent alien to logic. Scholasticism has made three creative elements to the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 ways: A) established a firm belief in God’s rationalism, viz. to believe that God has made a rational order and law in nature or in universe; and all natural beings, supervised by God, evolved in harmonious order regulated by God, and thus are understandable by human’s rational logic, which was given to the human being by God . B) fostered the sense of logical precision and exactness, which survived the scholasticism when the latter died out, and further transformed into the mathematical logic. C) helped to create man’s belief in the approach of systematic experiment in seeking the law of the nature and universe. It was through scholasticism that the great Greek tradition of logic was revived and passed into the modern science. Turning to natural phenomena of the logical rationalism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systematic experiments mar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inking ways of the modern science in Europe. Emphasis today should not solely be laid upon the theological character of scholasticism. Key Words: Scholasticism modern science thinking ways
作者简介:张绪山,1963—,1991-1999年留学希腊,就读于萨洛尼卡亚里士多德大学语言学院和艾奥尼纳大学历史考古学系,1998年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拜占庭史、中西交流史等,著有《6-7世纪中国和拜占庭帝国关系》(希腊文),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封建社会》等多部著作。
* 本研究完成于十多年前,曾得到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资助。其中部分内容以概要形式发表于《经济社会史评论》第1期,三联书店2004年。现在将全文发表,以呈现该成果的全貌。 [1] Creighto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1, Cambridge 1902, p. 2;转自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1页。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3页。 [3] 丹皮尔:《科学史》,第160页。 [4]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5]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5页.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9页。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0页。 [9] 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页。 [10] 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239页。 [11] 蒙克利夫编《圣殿下的私语: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书信集》,岳丽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12]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2页。 [13]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3页。 [14] 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83页。 [15] 《马克恩格斯论艺术》,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6页。 [16] 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43页。 [17]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页。 [18]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页。 [19] 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48页。 [2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页。 [21]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14页. [22]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23] 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页。 [24] 吴大猷:《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吴大猷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 [25]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4页。 [26] 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46-47页。 [27] 阎康年:《牛顿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67页。 [28] 阎康年,《牛顿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第467页。 [29] A. R. Mayer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IV, London 1969, p. 627.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3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14页。 [32]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2页。 [33] 艾金纳·吉尔森:中世纪哲学精神》,巴黎,弗林出版社1978年,转自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85页;L. Thorndike, The Survival of Mediaeval Intellectual Interests into Early Modern Times, Speculum, vol. II (1927), pp.150-152. [34] 索柯洛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论》,唐侠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35]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09-311页。 [36] 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第15页;丹皮尔:《科学史》,第199页。 [37] 阎康年:《牛顿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第483页。 [38] 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冀可平、钱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39] 丹皮尔:《科学史》,第150-151页。 [40] 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41]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147页。 [42]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87页。 [43] 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5页。 [44] 杜布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和自然》,陆建华、刘源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页。 [45]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09页。 [46] 梅森,上揭书,第102页。 [47] 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第15页。 [48]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1页。 [49]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84-585页。 [50]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58-359页。 [51] 埃伦·杜布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5页。 [5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323页。 [53]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第416-417页。 [54] 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第88页。 [55] 有关此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E. M. Sanford, The Twelfth Century — Renaissance or Proto-Renaissance?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aeval Studies, vol. XXVI (1951) p. 635-642;以及U. T. Holmes, The Idea of a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ibid., p. 643-651。 [56]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vol. 1,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repr. 1989, p. 103-104. [57] 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第211-212页;G. Makdisi, The Scholastic Method in Medieval Education: An Inquiry into its Orgins in Law and Theology,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aeval Studies, vol. XLIX (1974), p. 658-659. [58]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290页。 [59] 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第220页。 [60] 阎康年:《牛顿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第445页。 [6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78页。 [6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44-45页。 [63]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580页。 [64] 丹皮尔《科学史》,第153页。 |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