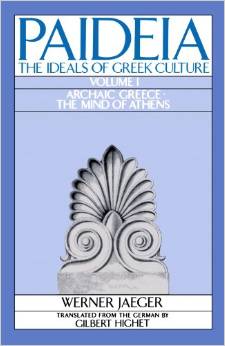| 吴晓群: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节选) |
| (发布日期: 2016-03-03 15:35 阅读:次) |
|
(德)瓦纳尔·耶格尔著 吴晓群译 前 言 本书是我1960年荣幸地就任哈佛大学卡尔•纽厄尔•杰克讲座(Carl Newell Jackson Lectures)教席时所做的系列讲座合集。为该教席命名的卡尔•纽厄尔•杰克逊教授将我引介到哈佛,这对我意味深长,使我能够在退休之时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教师,为此,我对他深表感谢。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中就这些讲演的题目做过简短的讨论。在此,呈现给大家的讲座合集则是对那些内容的进一步扩展,并辅有大量注释,以此作为一本著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即便如此,以现在这样从演讲内容扩展而来的规模也没有完全实现我原先的计划。当我写作《教化》(Paideia)一书时,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部著作应该专门有一卷篇幅用来描述希腊教化是如何进入早期基督教世界,并为其所接受的。然而,尽管拙作的大部分内容在古代基督教文学领域内都已有人做过了,但该书所涉及的广大范围仍无法实现我对整本书预先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仍无法在那本著作中将历史的延续和希腊教化的传统在古代晚期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以及发生的变化全面展现出来。现在,我不再确定我是否还能将此放在一个广阔的规模中来处理,我甚至放弃了达至这一目标的希望。目前我已对此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决定在这些讲演中设定一些主要的大纲,然后将它们作为一种对那个整体的补偿发表出来。 幸运的是,我们手中拥有丰富的东方文献,如《死海古卷》和上埃及纳杰哈马迪(Nag-Hammadi)地区发现的完整的诺斯替教派文集,以及学界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研究兴趣的突然复活,同时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应该彻底重新评估,在我们时代刚刚开始的几个世纪里对基督宗教-希腊文化及哲学的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第三大因素。我将这本小书视作这一全新尝试的第一步。 瓦纳尔·耶格尔 哈佛大学 1961年复活节 第一章 在这些讲演中,我不会将宗教与文化对立起来,视作人类头脑中两种不同的思想形式。正如标题所显示的,尤其是在今日,当诸如卡尔•巴塞尔(Karl Barth)和布鲁纳(Brunner)这样的神学家们坚持认为,宗教不是文明的一个从属部分时,就如同老派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们时常将艺术、科学以及宗教混为一谈一样。换言之,我不希望在提要中讨论宗教与文化的问题,而是要具体地谈到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关系问题。与古典学家一样,我将以一种历史的方法去讨论这一现象。我不想将希腊思想(如同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或帕特侬神庙里所表达的那样)与基督教精神(如同恩尼斯•瑞南(Ernest Renan) 从雅典卫城返回圣地时所做的那样)相比较。瑞南感觉自己被纯美和纯粹理性的崇高表现所征服,就如同他在卫城上热情洋溢的祈祷中所理解和赞美的那样。[1]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这个与他同时代的年轻人,既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同时还是一个狂热的狄奥尼索斯崇拜的信徒,他则将这种比较推到了一个极端,并且从一个古典学家变成了一个反基督的传教士。我可不想做这样的比较,反之,我要谈及希腊文化在基督宗教出现之时的情况,以及这两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初几个世纪中的历史性交汇。不过,在本书有限的空间里,我不可能谈到早期基督教艺术,也无法涉及古代晚期和早期教会的拉丁世界。 从18世纪下半叶近代历史意识的苏醒以来,神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在分析及描述那与新宗教的诞生一同开始的重大历史过程时,在所有的因素中,希腊文明在基督教思想中对确立基督教传统的最终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最初,基督教只是晚期犹太教宗教生活中的一个产物而已。[3]最近发现的诸如所谓《死海古卷》这样的古代文书,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犹太教投射了一缕新的光线,与之相应地,也在那个时代死海沿岸其他宗教派别的苦修式虔诚与耶稣救世主信息之间划清了界线。表面上,两者间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其实两者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事实上,基督教的“福音传道”(kerygma)并没有停留在死海或是在犹地阿(Judaea)的边界地区,而是超越了其排它性和地区孤立性扩散到了周边地区,这是一个由希腊文明与希腊语所统辖的世界。这在基督教的发展以及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扩张中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其先导是希腊化时代里希腊文明长达三个世纪的扩张,而这一时期长期以来都为古典学家所忽视,因为他们不肯关注除希腊古典时期以外的其他时代。约翰尼•格斯提•德鲁森(Johann Gustav Droysen)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他首先发现了希腊世界的扩张,他也是第一位书写其历史的人。[4]从他已出版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他被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义所激发,因为他已觉察到,如果没有这种希腊文化的后古典式演变,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是不可能兴起的 。[5]当然,在罗马帝国中,基督教在说希腊语世界中的这种发展过程并非是单方面的,因为同时它也意味着基督宗教的希腊化(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教被希腊化不是一件立即就很清晰的事情。我们力图将此解释得更为明确一些。 我们注意到,在使徒时代,在基督教希腊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使用希腊语,这表现在《新约》的写作之中,后使徒时代所谓的“使徒教父”(Apostolic Fathers)仍沿袭这种习惯。这也是“希腊主义”(Hellenismos)这个词最初的意思。[6]而语言问题决不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希腊语是被视作一个有关概念、思想范畴、承袭性的隐喻以及微妙的言外之意等这样一个整体进入基督教思想之中的。基督教之所以从第一代信徒开始就与其周边世界迅速同化,明确的理由显然是,首先,基督教是一次犹太运动,那些人是保罗时代被希腊化了的犹太人,这不仅是在犹太人流散时期,而且也包括他们大规模进入巴勒斯坦地区之后;[7]其次,正是那些被希腊化了的犹太人首先成为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使徒团体中被称之为“说希腊语的犹太人”(Hellenists),他们在其首领司提反(Stephen)殉教之后散布在巴勒斯坦各地,并从第二代开始了传教的活动。[8]如同司提反本人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叫斯特凡诺斯(Stephanos)一样,他们也都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诸如腓利浦斯(Philippos)、尼克罗(Nikanor)、普罗查诺斯(Prochoros)、泰门(Timon)、巴门尼斯(Parmenas)、尼克罗斯(Nikolaos),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来自被希腊化至少一代甚至一代以上的犹太家庭。[9]新教派克里斯蒂亚诺(Christianoi)这一名称就源于一个希腊城市安提阿(Antioch),在那里,那些希腊化了的犹太人为传播基督教建立了第一块活动区域。[10]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犹太会堂(synagogai)中,希腊语都是通用语言。这一点可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身上得到明证,他那些讲究修辞的希腊文著作不是为异教徒写的,而是为其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同胞写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后,大量新皈依的异教徒不理解,为何在离散地犹太会堂中举行的犹太崇拜仪式中会使用希腊语的原因。而保罗的整个传教活动都基于这一事实。他与旅途中遇见的犹太人谈论,力图将基督的福音以希腊语加以传播,并傅以精妙的希腊式逻辑论证。《旧约》中两段作为戒律的话语就均源自希腊文的《旧约全书》而非源于希伯来的源头。[11] 除了《耶稣语录》(the Logia)、《耶稣语录集成》和《福音书》(the Evangelia)的新形式以外,使徒时代的基督教作家也都效仿希腊哲学家的形式进行写作,[12]他们使用希腊文写作了《使徒书》(the Epistle)、《使徒行传》,以及由其弟子所记载的智者或著名人物的教诲和言行,等等。沿着这些线索,再加上其他类型的文献,诸如《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启示录》和《布道书》(the Sermon)等等,可见,基督教文学在使徒教父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替代了希腊大众哲学中讽刺与辩论学派(the Diatribe and Dialexis)的形式,希腊的这种大众哲学曾试图将犬儒学派(Cynics)、斯多噶学派(Stoics)以及享乐主义(Epicureans)的教义向民众传播。在埃及,甚至殉教史的形式也被异教徒们所利用,殉教史是在使徒时代当埃及人与犹太人之间发生激烈宗教冲突时发展起来的,在基督教殉教文学产生之前就已存在。[13]虽然,这些昙花一现的作品并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仍不得不将这些希腊化时代的宗教小册子看作是许多教派自我“宣传”(propaganda fides)的一种手段。柏拉图曾提及俄耳甫斯教派的成员挨家挨户分发其教义小册子的事情,[14]而普鲁塔克也在《给新婚人士的忠告》(Precepts for Newly Married People)一书中劝告女子,不要在后门接待那些试图偷偷向她们传播某种外来宗教的陌生人,因为那样可能会离间她与其丈夫之间的关系。[15]在《雅各书》中,我们发现了一条来自于俄耳甫斯教的短语——“诞生之轮”(wheel of birth) ,[16]这肯定是《雅各书》的作者从某些宣传俄耳甫斯教的小册子里撷取的。这些教派就如同一个大家庭,时常相互借鉴一些词语和说法。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 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宣扬“毕达哥拉斯学派式的”生活方式,使用“Y”作为他们的象征物,这是一个交叉道路的标志,意味着一个人不得不决定他要选择走哪条路,是做好人还是坏人。[17]在希腊化时代,人们了解这种教义有两种方式,当然是非常古老的方式(比如在赫西俄德的作品中出现的[18]),在一本大众哲学的文论《塞贝斯陶板》(Pinax of Cebes)中为我们描绘了神庙中奉献祭品的两种方式。[19]这篇文论充当了哲学道德说教的一个出发点,如同不可知之上帝的祭坛一样,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中将一篇铭文作为他抨击的对象。十九世纪发现的最古老的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被称之为《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 of the Twelve Apostles),该手册也将这两种方式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本质,这两种方式将洗礼和圣餐中的圣礼结合在一起。[20]显然,它们是被加入了一种基督教元素,因为这两种方式都来自于某些前基督教时期的小册子。这种带有道德格言的半文学形式的书籍和小册子,比如古希腊原子论哲学之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小册子《思想的宁静》(Peace of Mind)。该书开篇即说:“如果你想要享受思想的宁静,那么就不要涉足太多的活动。”这本书在当时非常著名,被时人广为传阅。[21]当我在《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中发现这一训诫时十分惊讶,因为它已被改造成了基督教的诫令:“戒除诸多活动,如此你便永远也不会误入歧途。因为那些忙于过多活动的人也会犯很多错误,而且由于他们投入各种活动之中,从而无法伺奉他们的主。”[22]因此,正如斐洛所常说的那样,他从其自身的经验中知道,“旧钱再次使用时会给它打上新的印记。”[23] 因此,正是早期基督教的使命迫使传教士或使徒利用希腊的文学形式和演说方法去应对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改宗的,且分布于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大城市之中。当保罗与异教徒相接触并使其改宗时,这就变得更加有必要了。在希腊化时期,这种规劝活动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希腊哲学的特征。各种学派通过规劝演说试图为自己找寻追随者,在这种演说中,他们都会极力推销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或教义(dogma),并声称那是达至幸福的唯一途径。我们发现,这种修辞法首先是出现在希腊智者们的学说中,以及柏拉图对话集中的苏格拉底之口。[24]甚至“改宗”(conversion)这个词也是源于柏拉图,表示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表达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25]即使这种接受的动机各不相同,基督教的福音宣讲中提及人的无知,并承诺上帝将赐予人类知识,如同所有的哲学思想一样,它将此归因于某个主人或导师,他拥有并揭示真理。这种希腊哲人与基督教传教士的类似做法可视作后者对前者的利用。哲学家的上帝与传统异教中的奥林波斯诸神也是不相同的,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体系为其追随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庇护所。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则追随着他们的脚步,而且如果我们相信《使徒行传》中的记载,那么,他们有时甚至从其先辈那里借用其辩论中的论据和论点,尤其是当他们与一个受过教育的希腊倾听者交谈时更会如此。[26] 这就是在希腊人与基督教徒邂逅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基督教未来之所以够成为世界性宗教也正是有赖于此。《使徒行传》的作者让使徒保罗去往雅典时,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雅典作为古典希腊世界的文化与知识中心以及历史传统的象征,保罗在庄严的阿瑞奥帕戈斯山(the Areopagus)上向斯多噶学派的听众以及伊比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们布道,向他们宣说那不可知的上帝。[27]他引用了一位希腊诗人的诗句,“我们都是他的子孙”,而他的辩论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多噶式的,且被认为可以说服某个受过教育的哲学头脑。[28]无论这一难忘的场景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戏剧性地再现了基督教世界与古典世界之间最初进行智力较量的历史性局面,这一幕都清楚地向我们揭示了《使徒行传》的作者是怎样理解的。[29]这种讨论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否则就是不可能的。保罗选择了希腊哲学传统作为这个基础,在那个时代,对于生活在希腊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来说,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稍后一点的基督教作家,即《使徒腓力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 Philip)的作者以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其写作意图:模仿权威的《使徒行传》,他让他的主人公来到雅典,像保罗一样针对相同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听众发表演说。他让使徒腓力说,“我来雅典是为了向你们宣示基督的教化。”而那正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想要做的。[30] 基督教呼唤基督的教化,模仿者们强调,使徒的意图是要使基督教成为古典希腊教化的一种延续,这对于那些拥有旧文化传统的人们来说是符合逻辑的,也是能够被接受的。同时,《使徒腓力传》的作者还暗示,古典教化将被一种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文化所取代 。由此,古代教化就成为了它的工具。 译者简介:吴晓群,1966—,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古代希腊史及西方古典史学。已出版专著三部,译著三部,发表中英文论文三十多篇。 [1] Ernest Renan, 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jeunesse (Paris 1959), p. 43f. [2] 理论上,希腊文明对基督宗教的影响在许多领域里已为学术性的神学论著所承认。在教义史上,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 I, Freiburg-Leipzig, 1894, 121-147.)将希腊文明列为对基督宗教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最有影响的因素之一。哈纳克基本工作的重要性尤在于展示了希腊哲学对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最近,H•A•沃尔夫森(H. A. Wolfson)对基督教的哲学含义与其希腊源头的关系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H. A. Wolfs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Fathers I, Cambridge, Mass., 1956.)。甚至在这种系统努力之前,追随哈纳克史学流派的神学家就已在《圣经》特别是《新约》中找到了希腊的因素,而汉斯•利茨曼(Hans Lietzmann)则在其主编的杂志《论新约手册》(Handbuch zum Neuen Testament)中系统地将这种观点运用于对最早期基督教文献的注释之中。近来,在考古学界,E•R•古迪纳夫(E. R. Goodenough)在其八卷本的《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符号》(Jewish Symbols in the Greco-Roman Period, 8 vols., New York, 1953-1958.)一书中揭示了希腊文明对晚期犹太教的影响。所谓的宗教通史已表明外来宗教对于早期基督教的影响是广泛的,同时也触及到了希腊人对早期基督教的影响。另一方面,以往的神学研究学派(诸如D•F•斯特劳斯(D. F. Strauss)学派)习惯上假设希腊哲学对《新约》特别是对圣保罗有着直接的影响,但这尚未被现代史学研究所证实。当然,这其中的确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但是,并不能将其视作一种明显的教义上的影响,例如,十九世纪中叶的图宾根(Tübingen)神学流派就曾假设塞涅卡(Seneca)对圣保罗产生了影响。总之,这种认为希腊哲学在教义上对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影响的观点是来自于后世的思想家,参见第64、86页以下的内容。对于古典文学以及文学形式的追述,参见第7、57页;至于犹太世界及犹太-基督教世界里的希腊语,则可参见第5-12页。 [3] 这方面被主要强调是因为,过去半个世纪里在基督教神学研究中,自哈纳克以来,学者们认为,有必要警醒并抵制R•莱岑施泰因(R. Reitzenstein)和其他当代学者所青睐宗教史(Religionsgeschichte)的趋势,因为他们的观点可能会对基督宗教的独创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并使其真正的起源在犹太思想史上仅仅作为其中的一个阶段,从而变得模糊不清。关于犹太教晚期的情况,参见 Emil Schürer,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im Zeitalter Jesu Christi (4th ed., Leipzig 1901-1909;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Macpherson, S. Taylor, and P. Christie, New York 1891). 也可参见R. Pfeiffer, History of New Testament Times (New York 1949). [4] J. G. Droysen,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Hamburg 1836-1843). [5] J. G. Droysen, Briefwechsel, ed., Rudolf Hübner (Berlin-Leipzig 1929) I. 70. 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到,显然,发现希腊主义之历史的人,其兴趣部分地是因为这个时期本身,而更多的则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它使得基督教成为可能。 [6] “希腊主义”(Hellenismos)一词为名词,它源于动词hellenizo,意为“说希腊语”,最初的含义是正确地使用希腊语。这一概念似乎最初只是为教授修辞学的教师所使用。在雅典莱森学园(Lyceum),西奥弗拉斯塔斯(Theophrastus)像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一样将修辞学作为他教学的一部分,以此来建构他称为“美德措辞”(aretai)之完美体系理论的五个部分,其中首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就是Hellenismos,即在使用希腊语时正确地运用语法,以戒除文理不通、粗鄙不堪的问题。(参见:J. Stroux, De Theophrasti virtutibus dictendi, Leipzig, 1912, p. 13.)这一要求有其时代特色,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外邦人的数量庞大,以至于他们说话的方式败坏了人们的口头用语,甚至对希腊人自己的语言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此,Hellenismos一词就不再仅有原初的含义,之后,它不可避免地承担了“采用希腊式风格”或“希腊生活方式”的意思,特别是在希腊之外当希腊文化成为一种时尚时。关于古代晚期的另一个用词则是大范围的基督教化,参见第72页。这不仅意味着希腊人的文化和语言,而且还意指“异教徒的”,即古希腊的宗教和崇拜仪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此意义上,它更多地被希腊教会的教父们在其辩论中加以运用。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在学术文献中并不总是能够被分辨得足够清晰。 [7] 当然,尤其是对于犹太贵族和知识阶层而言,这是真实的。参见:Josephus, Antiquitates Judaicae, XX. 12.264, (Opera, ed. Nies, IV, Berlin, 1890, 269.) 正如约瑟福斯所正确指出的:大多数犹太人比其他民族更不愿意学习外来语言,这与希腊化世界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犹太人不同,他们很快便掌握了希腊语,而不是埃及人的或其他民族的语言。但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希腊语使用之广,实则远远超过学者们所估计的,它不仅被用于商业贸易之中,对于受教育较少的阶层而言,即贩夫走卒之辈,亦通晓希腊语。参见:S. Lieberman, Greek in Jewish Palestine (New York 1942), and Hellenism in Jewish Palestine, (New York 1950). [8]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1节以下。在此出现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Hellenists)一词是与“希伯来人”(Hebrews)一词相对立的,但它并不是指“希腊人”(在《新约》中“希腊人”(Greeks)这个词通常是指“犹太人眼中的异教徒”(gentiles))。“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一词是对犹太人中那些说希腊语的人的正式称呼,因此,它也指使徒时代在耶路撒冷的早期基督教社团中的犹太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是生为犹太人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却接受了希腊文化的人,而是指那些不再说他们原本阿拉米语(Aramaic)的犹太人,他们即便是懂得这种原初的语言,然而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曾长期居住在希腊化的城市中,之后才重返祖居地的,因此他们说的仍是希腊语。那些人并没有变成基督徒,而是在耶路撒冷拥有他们自己的希腊式犹太会堂,我们发现有一个像司提反一样说希腊语的犹太基督徒曾与他们进行过长时间的神学讨论。《使徒行传》第六章第9节中曾专门提及利比里亚人(the Libertinoi)、昔勒尼人(the Cyrenaeans)、亚历山大里亚人(the Alexandrians)和西里西亚人(the Cilicians)中的犹太会堂,以及分布在小亚细亚各地所有的犹太会堂。自然地,这些说希腊语的基督徒,甚至他们在司提反死前仍在耶路撒冷传教,他们就应该首先转向犹太人中那些说希腊语的非基督徒,向其传教,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与教育的希腊背景。在每日分食及周鳏济寡等方面,他们始终坚持让通希腊语者为其代表。据此,可以断定,他们在使徒团体中,虽是少数,却势力日增。因此,他们能够从十二门徒那时获得任命新助祭的重要特权。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5节中第一批助祭都有着一个希腊式的名字,这似乎清晰地表明,他们的特别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是使徒社团中说希腊语的人,他们也应该是会众中主要受关照的那部分人。使徒宣布革新,强调的是让他们自己来做所有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如果新的助祭不需要得到整个会众的关照,那么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即使和“希伯来人”一样,仍增加了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在早期基督教社团中的重要性,因为七个被选出来的助祭全都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 [9] 只有尼克罗斯(Nikolaos)不是犹太裔,而是一位来自于安提阿(Antioch)的改宗者,参见:Acts 6.5. [10] Acts 11.26. [11] 在这方面,福音书与圣保罗之间有所不同。在圣保罗的书信中引自《旧约》(the LXX)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来自于其他源头的材料。参见:H. B. Swete,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2nd ed. (Cambridge 1944) p. 381ff. [12]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讨论参见:Paul Wendland, Die urchristlichen Literaturformen (Tübingen 1912), part 3 of H. Lietzmann’s Hand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I. [13] 参见:H. Musurillo, The Acts of the Pagan Martyrs (Oxford, 1954), 特别是p. 236以下。 [14] Plato, Rep. II. 364e. 柏拉图提及在由穆萨欧斯(Musaeus)的“漫游先知”(wandering prophets) 和俄耳甫斯所提供的“一堆书籍”中,他们教给人们一种利泻排毒的宗教,该宗教的仪式被称作“泰勒塔”(teletai),即入会仪式。在该段落(364b-c)之前,柏拉图曾说,这些先知们拜访富有的人家是想要说服他们改变信仰,【110】先知以仪式和献祭的方式来教导他们,使之从其旧有的罪或他们祖先的罪中得以赦免。这些书籍中包含了具体的劝告,各种达至此目的的方法。参见:O. Kern, Orphicorum Fragmenta (Berlin, 1922) p. 81f. [15] 这就是普鲁塔克的意思,见Praecepta coniugalia c. 19 (Moralia I, ed. Paton-Wegehaupt, Leipzig 1925, p. 288, 5-10).另参见本人著作:Scripta Minora (Rome 1960) I, 136. [16] James 3.6. 参见:Hans Windisch, Die katholischen Briefe, 3rd ed. (Tübingen 1951; Hand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XV) p. 23, and Kern, Orphicorum Fragmenta, p. 244. [17] 参见:Scripta Minora I, 140. [18] Hesiod, Works and Days 288-293. [19] 参见:Scripta Minora I, 140f. [20] Didache c. 1-6, in Die apostolischen Väter, ed. Karl Bihlmeyer (Tübingen 1924). 在《使徒巴拿巴传》(the Epistle of Barnabas) c. 18中也出现了对“两种方式”的大量讨论,见上书。因为在两份文献中对于材料的安排有所不同,因此两者不可能互为源头,更像是它们都依赖于一个共同的资料来源。这一来源显示其来自一本犹太教的训导小册子,而且有关这两种方式的文献的确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认为是基督教的。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塞贝斯陶板》(Pinax of Cebes, 参见注释19)中包含了同样的道德训诫,勿庸置疑,它来自一个希腊的源头,而非犹太教的或是基督教的。 [21] Democritus frg. 3, Diels-Kranz,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II 8.132. 该书的内容被后人进一步扩展,使之广为流传,并且该书的部分内容甚至进入了古代晚期的某些道德谚语和格言的集子中,诸如《斯托布阿斯作品集》(the florilegium of Stobaeus)。在罗马帝国时期,该书仍广为流传。【111】《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也是一本大众读物(Volksbuch),不同的文本传播也都已证实了这一点。参见:A Papyrus Codex of the Shepherd of Hermas (Similitudes 2-9), ed. Campbell Bonner (Ann Arbor 1934) p. 23ff. [22] Hermae Pastor, Sim. IV. 5, in Patres Apostolici, ed. Gebhardt-Harnack-Zahn, 4th ed. (Leipzig 1902) p. 171, 4ff. [23] Philo, e.g., Quod deterius potiori insidiari soleat, I. 292.24. [24] 苏格拉底式劝诫演说词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柏拉图的对话集《欧绪德谟篇》(Euthydemus)中;参见本人著作:Aristotle (Oxford 1948) p. 62f. [25] A. D. Nock, Conversion (Oxford 1933), 诺克在书中将新教徒的改宗与希腊化时代那些准宗教哲学派别的心理定势相比较。柏拉图曾将哲学与人转向真正存在之光进行比较,有关于此的论述可参见本人著作:Paideia II (Oxford and New York 1943) 285,特别是295ff. [26] 当然,之后,基督教的护教者们更是大规模地借用希腊化时代哲学家们的思想,例如,他们用哲学家们的辩论方法来反对希腊罗马大众宗教中的诸神。 [27] Acts 17.17ff. 保罗在犹太会堂里对犹太人和雅典的新改宗者发表演说,所以《使徒行传》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在阿雷奥帕格斯山向异教徒发表演说,因而是一次相当典型的使徒传教活动。这些在犹太会堂中的讲话仅被简单提及,但是保罗当然不会将其遗忘,因为犹太会堂是他布道时经常使用的场所。然而,这一次强调的显然是在阿雷奥帕格斯山上的长篇辩论,描绘了这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的新处境,保罗既是一位希腊文化的崇拜者本身又是一个犹太人,而他的最终目的却是要在古典希腊世界里传播基督教。 [28]对于保罗在雅典演说中所采用的辩论方式最全面的分析,及其与古代希腊传统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斯多噶派元素),可参见:Eduard Norden, Agnostos Theos (Berlin-Leipzig 1913) p. 13ff; 还可参见重印的本人著作Scripta Minora I, 110-111中对该书所做的评论。我不认同诺登华丽的论点,他认为《使徒行传》的作者肯定是使用了文学的形式来描述异教的布道者和奇迹创造者泰安那的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 of Tyana),将《使徒行传》一书写作的时间定在公元2世纪。在《新约》中,引用希腊诗歌的地方出现过几次。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一位基督教作家,他是第一个特别关注《新约》诸卷中引用希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作者。在他本人的著作中也充满了来自希腊诗人的诗句,其中有些直接来自于希腊诗人的文本,有些则是摘自于《名诗选》以及类似的选集。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对《圣经》作者的希腊教化问题有着极大的兴趣。他准确地辩认出《使徒行传》17.28中的引文是取自于阿拉图斯(Aratus)的天文学著作《现象》(Phaenomena)第五行(Stromata I. 19, ed. Stählin, Leipzig 1905-1909, II, 59, 1ff)。同样,他还指出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一首诗中的引文是取自于克里特人的史诗《神谕》(the Oracles)(frg. 1, Diels-Kranz, Vorsokratiker I. 31)中一封致提图斯(Titus)的信里(1.12) (Strom. I. 14, Stählin II, 37, 23ff);而《哥林多前书》15.33中另一段有关希腊的回忆则取自于最著名的新阿提卡喜剧诗人米南德(Menander)的作品(Thaïs frg. 218, Comicorum Atticorum Fragmenta, ed. Kock, III, Leipzig 1888, 62),保罗在一封致科林斯最博学的希腊会众的书信中十分适当地引用了米南德的这段文字。 [29] 了解古代历史书写传统的学者们丝毫也不怀疑,保罗在雅典的演说是一种典型的逼真记录,但并非是一份历史文献。作者如此写作是为了达到整本书的戏剧性高潮,他不仅研习了希腊的历史著作,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具有真正历史视野的人。因为很显然,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作者可以用这种方式将其材料与技巧圆融在文章的各个部分之中,以达到某种平衡。参见:A. v. Harnack, “Ist die Rede des Paulus in Athen ein ursprünglicher Bestandteil der Apostelgeschichter?” in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3rd Series, IX, No. 1 (Leipzig 1913).有关于将《使徒行传》的作者视作历史学家的讨论可参见:Eduard Meyer, Ursprung und Anfänge des Christentums (Stuttgart 1921-1923) III, 3 and 23. [30] Acta Philippi c. 8 (3).参见:Acta Apostolorum Apocrypha, ed. Lipsius-Bonnet, II, Part 2 (Leipzig 1903) p. 5, 2. 该文发表于《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
 首页
首页